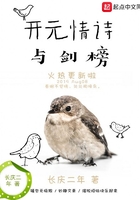
第12章 皇上,这首诗我不会写!
隋二世春光绚烂,张九龄秋桂皎洁
“回禀陛下,小民的诗已经作好了!”陈成恭敬回复道。
“哦?”
众人都看着他,明明一个字都没见你写,结果你说已经写好了?
“那你把诗给大家看看吧!”李隆基吩咐道。
“回圣人,此诗写不得。”陈成愈加恭敬。
“那是为何?”李隆基忽然想到这小子的“书法”不堪入目,难道是想规避一笔烂字带来的不好观感?“要是这诗写不得,那你就念给大家听听吧!”
“回圣人,这诗也念不得。”陈成继续回道,让众人更摸不着头脑来!
“书也书不得,念也念不得,难道你这诗是要猜的不成!”李隆基哭笑不得。
“不猜不猜。”陈成道:“这诗我只能悄咪咪地念给张丞相听,只念给他一个人听。若不然,念出来定会叫诸位师长说小民‘言不由衷’。”
几番胃口一吊,众人就更好奇他这诗是什么样的,如果换别人,也许就不由着他瞎胡闹了,可是念给张九龄听,以他的性格,自然不会和陈成一起瞎胡闹,反而让人期待老张听完陈成诗的反应。
“那你就念给他一个人听好了!”李隆基不为难他,问晾在一边的王维道:“卿之诗可与众人观否?”
“有诗在此。”王维率直多了,将笔搁置,写完的作品一字不改,显出他格外自信。
“嚯!王老师竟然已经写完了!还写得那么长!那么多!”小陈瞥了一眼内心难免沮丧,暗地里投降了一半。
皇帝猜的不错,陈成的诗之所以写不出来,的确是不想再用自己难看的字来丢人现眼。
而要念出来的话,万一才说一句,就有人跳出来说“你这个抄袭大王!”那就彻底歇菜了!
陈成还在做激烈的心理斗争,但王维的诗已经展现在众人面前,光是一手精妙的书法就令殿中诸臣褒赞不已,再去看诗,更加激赏!
张九龄说“东都近来以王摩诘诗文为佳”,绝不是无的放矢!
王维写的还不止一首,一写便是两首,上书《献始兴公》的标题。
张九龄家乡岭南始兴县,封爵始兴县子。
其一
珥笔趋丹陛,垂珰上玉除。
步檐青琐闼,方幰画轮车。
市阅千金字,朝闻五色书。
致君光帝典,荐士满公车。
伏奏回金驾,横经重石渠。
从兹罢角牴,且复幸储胥。
天统知尧后,王章笑鲁初。
匈奴遥俯伏,汉相俨簪裾。
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
其二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中流。
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
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
任智诚则短,守任固其优。
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小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
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两首诗笔法严密,一丝不苟,典故频出,对仗精谨,一看就是行家手笔。
王维偌大名声,状元及第,但诗中态度谦逊,品质高洁,诗中表露出的“不为一己之私,但为苍生造福”的渴望,也真诚可信,正是向君子投诚的绝佳作品!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中流——有此句,正是投张相所好!与张相本人诗句亦颇有类同。”
“此等才气,张相不用,怕是外人也要见怪了!”
众人纷纷议论着,以王维之才,搏杀陈成这等黄口小儿并非难事,若是得到张九龄赏识,仕途上再进一步,那倒是能传为一番佳话。
“给张曲江吧!”李隆基摆摆手,让高力士把两首诗交给张九龄。
张九龄仔细阅读,并未多说,频频点头,却也不难看出他对王维的才华十分欣赏。
“陈苌到你了!”李隆基挥挥手,示意陈成该上了。
陈成只能硬着头皮,一步一步走向诗坛大宗师、也是帝国宰相的张九龄面前。
从他弱小的身材,不自信的气度,跟王维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几番想要开口,可是嘴里不知道嗫嚅着什么,最后又吞了回去。
“但说无妨!”张九龄语气和煦。
“好!”陈成终于鼓足了勇气,凑到张九龄面前,含含糊糊地说了五个字。
“你说什么?”张九龄眉头一皱,表示没听清。
“%¥¥#——”陈成只能又重复了一遍,紧紧盯着张九龄的反应,生怕出现不妙的结果,让他当场将自己叉出去。
“然后呢?”
“#&%*¥——”陈成又念了五个字。
张九龄点点头,示意他继续念下去。陈成心中的弦松了几分,总算流利起来,将五言八句、40个字的诗念与他听。
张九龄听完之后,若有所思,然后又忍不住盯着陈成多看了两眼,直让他心发毛。
本来王维的诗作,众人看了又看,击节赞赏,不吝溢美之词,以张九龄的反应,也是挺欣赏的。如果换了自己,这诗就直接不写了,投笔认输吧!
可宰相听完之后,竟然陷入了思考,难道陈成这诗真有点名堂?
对陈成来说,这诗不是有点名堂,而是太有名堂了!所以当他念出前五个字的时候,心脏都要跳出来,简直就像杨子荣与座山雕对暗号“天王盖地虎”那一段!
他对张九龄说的五个字是:
兰叶春葳蕤。
兰草逢春,枝叶繁茂!
这不是非常普通的句子吗?有何可怕?
问题是,这五个字正是张九龄自己写的啊!
别说这五个字,余下的35个字,悉数都是张九龄写的!
也就是说,陈成当着原作者张九龄的面,抄了一首张九龄的诗!
这也是陈成说这诗写不得、念不得的原因!
你想啊,如果堂而皇之地把整首诗写出来、念出来,张九龄忽然来一句:“这特么不是我的诗吗?你小子找死?抄你大爷头上了?!”那可就全完了!
知道正主在场,那陈成吃了熊心豹子胆,还头铁抄张九龄的诗?
不不,陈成是赌在开元二十四年的此时,这首诗张九龄还没有作出来!
“既然当众念不得,”张九龄轻吐口气,目光灼灼地盯着陈成:“那书得否?”
陈成无法应对,只是讷讷点头。
“取纸笔来!”张九龄一声吩咐,周遭立马来人服务相爷,可张九龄并没有让陈成动笔,只见他自己大笔一挥,龙飞凤舞,片刻之后宣告功成,命人将字幅展现给众人看!
陈成看去,心脏一簇,险些就要骤停!
张九龄要夺回其诗作的原著权吗?
“非书不得,非念不得,实则折不得。”张九龄微微一笑:“此则陈生《感遇》之诗也!”
字幅中,正是《感遇》全诗四十字!
“啊!”陈成头晕目眩,幸福得无法言说!
听到没有!原作者说了,这是“陈生之《感遇》诗!”
而且落款分明是“颍川陈苌作,曲江张九龄书”!
公开盖章陈成的“著作权”!
“快快!看看陈十一写了什么?”
“为何说是‘折不得’?”
殿中好奇的众人都把脑袋凑了过去,想要一睹为快。但是圣人在堂,自然要让天子先过目。
李隆基大是快慰,一览无余,全文写的是:
感遇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不自藻饰,自有词气!”天子看毕一番感叹,正要传播下去,见小李瑜一脸“好奇宝宝”的样子盯着字幅,便挥手让她先看。
小姑娘看着看着,眼神也不自觉暖了起来,颇受诗中感动。
再传诸人,张九龄之书法,陈十一之诗文,相得益彰,一气贯之,似乎本来就应是出自一人手笔!
称赞声不绝,让陈成紧攥半天的心不断舒展,喜悦溢将出来!
嗯,张丞相啊张丞相,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
但今天,我好像赌赢了!
其实张九龄接过诗来,当即心中一突,总觉得这字句,这手法,多么熟悉,与自己如出一辙!
是不是自己曾经写过的旧作?
可是仔细检索,也没有想到自己有写过这首诗,只能感叹自己与陈成“如有神交”,更加慨叹不已!
《感遇》诗一共有十二首,都是日后张九龄遭谗言贬谪后所作。
陈成抄的这首不仅是《唐诗三百首》的第一篇,也是这一组诗的第一篇,有点“开宗明义”的意味。
诗的大意是说:
春天的兰花草叶繁茂,秋天的桂花晶莹明亮。世间的草木勃勃的生机,都顺应了美好的季节。
谁想到山林隐逸的高人,闻到芬芳因而满怀喜悦草!
但,草木散发香气源于天性,怎么会求观赏者攀折呢?
当年雄心勃勃地说要背下整本《唐诗三百首》时,看到这开篇的第一首,并没有看出来这诗好在哪里,又凭什么排在首页。单纯是张九龄位高权重?
让小陈这样附庸风雅的人去看,必须要是先去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或者“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作来。
如此平淡的诗,就如白居易的很多诗,陶渊明的很多诗,都平淡到无趣,甚至没有“诗味”。
张九龄的诗除了那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大部分让平常人看来都挺寡淡,甚至“海上生明月”一联后余下的三联也都挺平淡。
陈成自认为“土猪吃不了细糠”,实在虽不知道张九龄诗好在哪里,但他一直在想:
张九龄自己写的,必定是最符合他的艺术偏好和追求吧?
出于这种思考,从一开始,陈成就考虑用这首诗,但是“当面抄袭被戳穿”的恐惧过不去。直到圣天子亲自摧搞了,再作不出皇帝的兴致也过了,才当机立断要用此诗!
陈成记得在自己那本少儿版的《唐诗三百首》的题解中看到,《感遇》诗是张九龄晚年表达对自己不再被重用的忧愤,以及对唐玄宗疏离自己的不满。
那肯定不是现在写的!
结果,他赌对了!
李隆基看到下面颇多称赞的场景,兴致又高了一层,便问张九龄道:“各自的诗作已经过目了,爱卿现在可已有了计较?”
是啊,两人的作品都很高妙,王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中流”不俗,陈成“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高洁,胜负,还真难评断!
张九龄沉吟良久,难以决断。
为何陈成看不出这首诗的好,而张九龄却赏爱不已?
让陈成看,这诗第一句,就有很大的“毛病”。
一会儿春天,一会儿秋天,刚刚兰花才开了,那边桂花已经“皎洁”了!
这不就是东一棒槌,西一榔头,想到哪里就写哪里吗?
也没有个实景啊!
对陈成来说,写景就应该是“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可以夸张点,但你也要眼前实际看到!
但这就是他不懂了。
中国诗歌,从《诗经》起,就好用“比兴”手法,以彼物比此物;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也就是:我想说一个道理,但我不会直接写出这个道理,而是用一个类似的东西去比喻,然后引起我想表达的情绪。
诗一开始就用了整齐的偶句,突出了两种高雅的植物,春兰秋桂,如屈原《九歌·礼魂》中“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的句子。但张九龄老家广东多桂树,他就把菊改成了桂。这从陈成“客观就是美”的朴素观点来评断,反倒还真是追求事实。
诗的传统从诗经来的,“比兴”在历朝历代都会被认为是最正统的创作手法,更被张九龄这样的文坛宗师看重。
等到第二句,说兰、桂各自在适当的季节,显示它们各自优秀的品质,这又是以此代比,联系现实了!
什么是适当的季节?太宗贞观年间,玄宗开元年间,这就是好的“季节”!所以太宗朝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玄宗朝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都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在这时节展露头角。
作为反例就是,隋炀帝时期有一大批能人,其实跟后来李世民用的是同一批,但明显那些人在杨广时代就没有发挥作用。
到第三联就“奇峰突起”了:“谁知”突然一转,这就引出了山林中的“美人”,那些喜爱兰桂风致高士!
有的人一看到“美人”就笑,但不是色色的笑,而是想到了楚辞中众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的“美人”,表面上写夫妇关系,实写政治君臣关系。
屈原的“美人”是楚怀王,张九龄的“美人”自然就是玄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