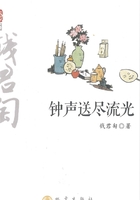
第10章 《豫堂藏印甲集》序言
记得距今三十年前,传闻天津有一批赵之谦所刻的印,其底细则略焉不详。因为我对赵氏刻印有偏好,当时颇想罗致,但是沪津相隔较远,无人为引,只得罢了。1952年盛夏,不意中在上海见到了这些印的一本没款谱,曾一度引起我对它早已淡忘了的罗致之念。到1955年6月,我因工作入京,与鉴家朱咏葵氏常作学术上的探讨。一次偶然谈到刻印,他告诉我这些印在天津的情况。我听了非常兴奋,很想立时一见。京津虽然近在咫尺,但是因为没有时间,无法去看,直至这一年的冬天,偶然得到一点闲暇,才和他同去天津。在一个雪天的窗前,把这些印细致地摩挲了一番。终因协议未成,废然而返。次年我又回到上海。此事我以为已经绝望,可是由于咏葵的不断努力,在除夕前数日出于意外地成功了。积久的愿望,一旦实现,真使我狂喜之极。
印的总数是一百零一钮,大半是青田石和寿山石。石质都是纯良的。其中有十六钮,作者没有署款,我不揣孤陋,断断续续在三年内为之补刻了。这些印部分曾见于清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前后傅栻(子式)所辑的四卷本《二金蝶堂印谱》,其后复见于清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徐士恺(子静)所辑的八卷本《观自得斋印集》。编拓本书时,我把它删去了一部分,共存九十五钮。
本书编次,以各印的制作先后为序。遇到款中没有年月的,则从其印面和款字的技法,以及他在各时期所用的名号等来区别插人。编次后,可看到这些印最早的如第一二两页“赵之谦印”和“益甫手段”,作于甲寅(1854年,咸丰四年),最迟的如第八十二页“朱志复字子泽之印信”,作于甲子(1864年,同治三年),前后亘十一年。虽然其间有好几年的作品尚付阙如,但是在这十一年中他刻印的历程,已经很清楚地在目了。
赵之谦的刻印,最初是从浙派入手的,后来才趋向皖派。他在皖派的基础上再益以碑碣钱镜文字,突破了邓石如、吴让之的樊篱,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卓然成为一家。他在刻印艺术上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后来的徐三庚、黄牧甫和吴昌硕等,都曾受他的影响。
赵之谦的刻印,有笔有墨,和仅有刀与石的不可同日而语。他对于文字的选择和组织,常是苦心经营,所以能够结构谨严,变化无穷,在分朱布白的处理上有独到之处。由于由浙人皖,他的刀法能够在巧中见拙,朱文劲拔凝练,白文沉雄朴茂。绝无尘俗之状,而有隽永之味,真正做到了“书如佳酒不须甜”的意境。赵之谦作的款字,除早岁外,尤其在他的晚年,杂诸龙门造像中,可以无分彼此。他在一个自用印上夸为“汉后隋前有此人”,可以说是他的自自。在边跋中,他又喜作铭记事,或附刻所为诗,这也丰富了他的边跋的内容,比仅署一名,更能增加欣赏者的联翩浮想。
赵之谦不但在刻印上有卓越的成就,就是在绘画上、书法上也同样有卓越的成就。他在近百年来的艺术园地里,的确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大家。
我在编拓本书时,除自藏外,复向友人张鲁庵、葛锡祺、矫毅诸氏借拓了若干钮,列为附录,意在更多地更全面地保存和流传赵之谦的刻印艺术。
本书如果没有张鲁庵氏供给上等的纸张和自制的印泥,没有符骥良氏用了很长的时间,精心地拓墨,是无法问世的。我在这里谨向他们以及惠借赵刻的诸氏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1960年10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