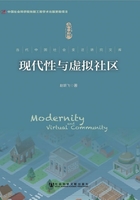
第一章 作为观念、心态和行为模式的现代性
第一节 关于现代性
现代性的问题悠久而复杂。从词源学角度看,在公元5世纪,西方就开始使用现代(Modern)一词。据考证,该词来源于拉丁文modernus;一般认为在英语中从17世纪开始得到运用;而在法语中则是1849年首次出现在夏布多里昂的《墓中回忆录》中;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1863年发表的论康斯坦丁·居伊的论文中首次明确地对现代性进行了表述(卡林内斯库,2002:55)。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的发展,现代性涉及越来越多的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来自哲学、美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持久探讨。然而,关于什么是现代性这一问题,至今尚无统一答案,“许多作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或对它们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界定。这些用法和界定,有时候不仅互不相同甚至还完全相反,常常令人困惑不已,不知所从”(谢立中,2001a)。虽然本书并不专门于研究现代性概念的历史,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梳理这些理论来获得现代性概念的轮廓,明确所使用概念的含义,从而为研究奠定一个相对坚实的概念基础。
从有关现代性的研究文献看,国内外研究者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表述异常丰富。这些表述既涉及到不同学者术语使用上的偏好,也涉及不同学科对现代性思考角度的差异,同时还涉及对概念本身内涵的实质性认定。
一 术语学意义上的差异
何谓现代性?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术语学问题。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指出:“‘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这些词在法语、英语、德语中并不具有统一意义。它们并不指向清楚、明晰的观念,也不指向封闭性的概念。”(贡巴尼翁,2006:232)其实,在同一种语言中,这些词语的内涵也不尽明晰。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一是现代性与现代、现代化、现代主义等相近概念的区别;二是现代性是一个对特定历史的描述概念还是一个与“古代”或“传统”相对应的概念——或者用谢立中的说法,是一个特指或者是泛指的概念。
从字面上看,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等多个相近的词语。一些学者对此曾经进行过讨论,指出在概念的应用上存在差别。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对现代化、现代主义以及现代性作出了区分。按照他的说法:“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从现代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它们: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刘小枫,1998:3)谢立中也曾经对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现代化这四个概念进行过讨论,并引用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观点,指出西方文献中大体的倾向是将“现代”看成一个比“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而将“现代性”界定为“现代时期” 或“现代状况”,将“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将“现代化”界定为实现“现代性”的一种过程(谢立中,2001a)。《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的译者则指出,在西文文献中,modernity一词有三种意义,分别作为时期(Period)、特质(Quality)和经验(Experience),“作时期时,当译为现代较妥”[1]。此外,现代性在有些时候还和现代主义、现代等词互相换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较为复杂。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曾指出,虽然现代性一词从17世纪即在英语中流行,但由于法国新古典主义传统关心语言的纯粹性和规范性,直到19世纪前半期,现代性(Modernité)一词才开始被使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法语的词典中没有Modernité一词。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Modernisime)“既用在宗教意义上,也用在广义的艺术上”(卡林内斯库,2002:338)。于是,19世纪以前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风格一度同文学艺术的现代性等同了起来。在中文语境下,学者们在使用相关概念时,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举例来说,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的名著《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其英文原版名为Exploring Individual Modernity,在1995年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译者使用了“现代化”一词与modernity对应,然而,细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所谈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刘小枫、谢立中等学者分析为现代性的东西[2]。以笔者的观点看,刘小枫、谢立中等人的理解更加符合英文构词法的一般规则和逻辑,也较为符合英译汉的对应规则。
很多学者都指出了现代性这一概念所表征的时间维度差异[3]。按照谢立中的分析,广义上的现代性指“新奇性、飞逝性”,而狭义上的现代性则指“17世纪以来的新文明” (谢立中,2001a)。前者的定义实际上无异于波德莱尔的著名论断,“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这样的理解实际上在表明,所谓现代是一个相对概念;而后者则可以认为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主张有关——“现代性指社会生活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吉登斯,2000:1)。实际上,许多西方学者曾经考察现代性的概念历史。在20世纪前半期,现代性的概念曾经和“新”的概念要素一度等同,这一倾向在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诗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但就其传统来讲,在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都存在着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rmas)在1981年的《现代性对后现代性》中提出:“一些论者把‘现代性’这一概念只限于文艺复兴。从历史角度看,这种限定显然过于狭隘了。比如,12世纪查理大帝时代,人们就认为是现代了,17世纪后期法国著名的‘古今之争’时期,人们也持同样的看法。”(哈贝马斯,2006:138)而尧斯(Hans Robert Hauss)则更加全面地回顾了西方历史上自5世纪以来的关于现代概念的应用,指出在罗马时代、中世纪经院时代都存在着关于现代的观点(尧斯,2006:149)。显然,从这种对现代性的理解出发,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在启蒙运动之前即有一个历史的谱系;而按照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的描述,现代性则是意味着断裂后的历史,是在工业革命后首先出现于17世纪欧洲社会中的一种突生性质[4]。
二 学科的惯习
如果对不同学科关于现代性的讨论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各个学科乃至各个学科的内部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尽一致。这种不一致比较清晰地体现在对现代性内涵和特征的界定上,同时也体现在对现代性的历史发生过程判断上。
(一)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
从哲学角度看,现代性与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道德、宗教、政治哲学紧密相关,哲学家们往往沿着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关于现代性研究的传统去探讨现代性的哲学本质,并将现代性与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有研究者指出,从哲学角度看,现代性态度的核心是理性和主体性,其根本价值则是自由,现代性表现为世俗化和“去魅”的过程(陈嘉明,2001:1-10)。对于此点,可以从康德和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找到证据。在哲学家中,康德和福柯先后写下了题为什么是启蒙的文章。康德在其《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提出,启蒙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运用理性的勇气,二是运用理性的自由。这一文章被福柯称为“现代性态度纲要”。而福柯自己则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并且,“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出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他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精神气质(ethos)”(福柯,1998:430)。这种态度在启蒙时代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气质,即批判的精神,“他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时代的永恒的批判”(同上:434)。
康德之前已经有不少哲学家涉及了上述现代性意义下的种种主题。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洛克(John Locke)、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休谟(David Hume),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笛卡儿(Descartes),荷兰的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以及德国的莱布尼茨(Leibnitz)等思想家,分别探讨了人的认知能力、知识确实性、自由等问题。笛卡儿关于“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题可以看做近代哲学家最早思考人的主体性的佐证,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也成为启蒙运动的理论大旗(梯利,2004:261-399)。康德在纯粹的哲学层面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人的主体性、理性以及科学和道德的原则问题,这一论述是以思维和行为规则的“先验性”为特征的,表达了他关于理性的态度。在康德之后,黑格尔、韦伯(Max Weber)、哈贝马斯、福柯等思想家进一步扩展了康德提出的论题。
黑格尔对现代性概念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进一步明确了主体性在现代性哲学分析中的地位,二是提出了市民社会理论。这两点分别表现在他关于自由的哲学思想和实体论中。“一般来说,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而所谓自我关系,“就是将自身作为客体的主体关系”。市民社会则是黑格尔所讨论的三大伦理范围之一,他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范畴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认为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阶段,同时市民社会的存在必须以国家为前提。在黑格尔眼中,市民社会具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建立在契约性基础上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活动领域,二是市民社会是联系个体和国家的重要中介组织(陈嘉明,2001:84-115;哈贝马斯,2004a:27-48)。
韦伯关于理性在现代化社会的扩张分析影响深远。它不仅是理解现代性内蕴的重要维度,也是关于现代性命运讨论的重要理论源泉,同时,它还和多元现代性的讨论紧密关联。在现代性问题上,称韦伯为哲学家或许有些牵强,因为他至少不是以一种纯粹的哲学式讨论来探讨现代性问题,但其讨论的主题沿袭了理性这一重要主题。简言之,在韦伯那里,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文化领域内表现为宗教世界观图景消除后的世俗化过程,在社会领域内表现为理性经济行为的蔓延以及科层制在各种组织的日益广泛应用,而个体的理性化则是在新教伦理影响下所形成的天职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指导作用。不过,韦伯关于“无意义的铁笼”的论述也表达了他对理性化远景的悲观预测。
哈贝马斯则是一个对康德以来的现代性思想进行全面继承和发展的人物,他也是在过去20多年中与各种后现代理论作家就现代性问题进行理论争辩的重要人物。从梳理现代性概念内涵的角度出发,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分析最重要的贡献应该包括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他在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观点基础上作出的三种世界的区分,即“客观世界”(Objective World)、“社会世界”(Social World)和“主观世界”(Subjective World),并进一步把贾维(Ian Charles Jarvie)在波普尔关于世界区分基础上所形成的行动分析作为出发点,提出了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的区分(哈贝马斯,2004b:75-93)。这一区分修正了韦伯将理性局限在工具理性层面的思想,其意义在于明确提出了现代性具有多重的内涵,即所谓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区别[5],并为他进一步提出沟通行动理论奠定基础。哈贝马斯的第二点贡献在于提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在韦伯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从表面上看反驳了后现代主义者关于“现代性终结”的观点,但实际上使得现代化过程与现代性从西欧起源的历史中分离开来,从而出现新保守主义立场那样“摆脱现代性的自我理解的文化外壳”的现象。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内部存在着自我更新的因子,从而使现代性问题在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下获得学理上的支撑。
(二)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6]
在美学和文学艺术研究等领域中,对现代性的理解有着另一番复杂景象。卡林内斯库指出:“美学现代性应该被理解成为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观点——对立传统;对立与资产阶级文明(即其理性、功利、进步理想)的现代性;对立于它自身,因为它把自己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卡林内斯库,1987:16-17)这一论断实际上是对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在文艺复兴以来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它指出了美学现代性内在的基本关怀取向。此外,有学者认为,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可以从来两个方面探讨:一是审美价值的现代性品格;二是审美趣味在现代性的心性结构中的扩张(吴予敏,1998:148)。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好与卡林内斯库所言的前两个方面相吻合。
对立传统,或者说审美价值的现代性品格主要是指在启蒙运动早期对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以及与基督教美学的对立。基督教神学美学坚持扬弃肉身感受,而人文主义则将美还原成日常生活,启蒙运动中对主体的强调为美学推崇感性奠定了在哲学上的合法性基础。这一推崇在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那里表现为对感性世界的完整追求,在席勒(Friedrich Schiller)那里则表现为对一种表现崇高理念的感性的颂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以极大的热情颂扬人的主体性,其区别则在于对待理性的态度。在歌德那里,感性是纯粹的;而在席勒那里,感性与理性以康德式的方式统一在一起。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以后,感性彻底压倒了理性,美带给人们的不再是灵魂的升华,而是生命过程的纯粹快乐(吴予敏,1998:146-150)。
美学现代性的第二点是审美趣味在现代性心性结构中的扩张,也即在个体的心理层面出现审美化的倾向。这一点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方面是源于哲学上主体意识的高扬。当宗教性的世界图景消失后,凡俗化的世界本身成为人们生存的意义所在,由此带来的是此岸感的高涨,也即主体性的生存感。从根本上说,“审美性乃是为了个体生命在失去彼岸支撑后得到此岸的支撑”(刘小枫,1998:301)。另一方面,如卡林内斯库指出,西方历史上的现代性包含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成分: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表现为资产阶级早期的那些杰出传统,如崇尚科学和理性、抽象框架中的自由理念;另一种则是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始自浪漫主义,并一直作为资产阶级标准的对立面出现,公开拒斥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卡林内斯库,2002:48)。在卡林内斯库看来,这种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一直将审美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从时间角度分析,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截然对立的时间观,即一种是资本主义文明关于客观化的、社会性的可测量的时间,另一种则是个人的、主观的时间观,也即自我所感受到的时间。卡林内斯库指出,在波德莱尔提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之前,司汤达(Henri Beyle Stendhal)在《意大利绘画史》中对“古代美”和“现代美”作出了区分:“他的‘浪漫主义’概念不仅含有明确信奉一种美学纲领的意思,而且含有对于现实性和当下性的感觉”;到了波德莱尔那里,“现代性是艺术昙花一现、难以捉摸、不可预料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不可改变的……”;而波德莱尔之后,“关于现代性转瞬即逝、变化不止的意识压倒并最终根除了另一半,传统遭到日益粗暴的拒绝,艺术想象力开始以探索和测绘‘未然’之域为尚”。由此观之,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是现代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反映了与时间问题直接相关的理智态度”(卡林内斯库:10-11)。
(三)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
在社会学中,对现代性的理解显得更加复杂多样。这种复杂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社会学有许多分支学科,二是和不同学者的研究兴趣、接近问题的策略紧密相关,有时候还不得不归诸他们所处的时代。笔者试图将这些关于现代性的研究按照其着眼点的不同归为三个大类。
第一类是从制度角度入手的观点。这一类研究强调制度变迁在现代性分析中的中心地位,同时把现代性视为经历程度不同的变迁过程后的社会所具备的特征。下面这一段话很好体现了这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性的理解图式。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过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过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周宪、许均,1999:“总序”)
上面这段话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指出了现代性概念的内在复杂性,但无意之间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对现代性的定义已经和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制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由此种路径出发理解的现代性是所谓“狭义”上的现代性。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也曾指出可以从四个维度对传统和现代进行区分,一是权力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二是有没有建立在货币基础之上的经济以及受自由市场制约的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消费;三是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固定分层被动态的社会分层所取代;四是宗教世界观的衰亡和个人工具理性的流行(霍尔,2006:43)。很显然,持类似观点的学者更多是将现代性与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典型社会变迁历程相关联,并往往进行 “传统”和“现代”的比较。这种思想可以从经典的西方社会学思想家那里找到痕迹,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关于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分,涂尔干(Emile Durkheim)关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辨析,韦伯关于理性化过程的分析以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关于模式变量的分析,都和这种观点有着内在的联系。回顾刘小枫关于现代现象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分析正是在“政治—经济”制度层面上对现代现象的透视,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宏大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层面上的制度变迁。而所谓现代性就是具备这样一些制度的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第二种观点关于现代性的社会学分析是从个体的态度和主观感受分析现代性问题,由于人的主观感受和价值观念以及意义相关联,其很多时候也被归到文化研究的领域中。美国社会学家伯曼(Marshall Berman)的这一段话明确地表明了这种对现代性的理解——“今天,全世界的男女们都在分享着一种重要的经验——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活中的种种可能与危险的体验。我将把这些体验总称为‘现代性’”(伯曼,2003:15)。虽然伯曼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个描述,但这种关于现代性的分析思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舍勒(Max Scheler)和齐美尔(Georg Simmel)就开创了研究个体心性结构的传统。舍勒深受现象学的影响,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包括社会制度和精神气质,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型的价值秩序的成形,改变了生活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转引自刘小枫,1998:16)。至于齐美尔,一般被认为他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先驱(Smith,2001:20-21)。在19世纪末,齐美尔开始关注城市生活和货币的研究,在以《货币哲学》和《大都会和精神生活》为代表的作品中,他详尽地探讨了货币、消费等现象的文化意义,对都市人群的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齐美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甚至当作一个内心世界)来体验[das Erleben]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只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弗里斯比,2003:62)。弗里斯比指出,齐美尔以及后来的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均是在波德莱尔所言现代性的意义上进行讨论,其视角十分相似。“他们的现代性分析的共同点,是经常无意识地接受现代性概念创始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所刻画的特征,即‘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同上:5)在这种视角的关照下,分析者往往从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出发,分析其背后所蕴涵的结构上的意义。如齐美尔认为,“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生命的总体性”(同上,66);克拉考尔提出,“一个时代在历史中占据的位置,更多地是通过分析它的琐碎的表面现象而确定的,而不是取决于该时代对自身的判断”(同上,142)。同样,本雅明拒斥所谓的整体景观,坚持所有的现象都是万花筒中的碎片。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关于消费的一系列研究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碎片化”分析传统之上。按照伯曼的分析,这种被称为“碎片化”(Fragment)的分析策略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从商品角度对资本主所作出的分析,正是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伯曼,2003:22-23)。
在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还存在另一种对现代性的理解,那就是个人现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所谓个人现代性(以下有时简称现代性),是指现代化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模式。”(杨国枢等,1989:243)这种对现代性的理解实际上和齐美尔等人在20世纪初开创的传统颇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这种理解也强调行为模式;相比之下,齐美尔等人更多地强调观感和心态。
关于个人现代性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现代化研究风行全球的时候。当时的学者认为,社会现代化(Societal Modernization)是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变化;而个人现代化则是社会个体在价值观念、工作习惯以及生活习惯方面的变化。个人现代性指的就是个人现代化的内涵。(杨国枢等:242-243)
(四)关于后现代性的一点讨论
现代性与后代现代性具有紧密的关联。二者存在于一套话语体系之中,并且二者的意义存在互参情形。从进一步理清现代性理解路径的目的出发,此处对后现代性进行简略讨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后现代问题的讨论广泛地存在于多个学科之中。和现代性概念一样,后现代性概念也有较长的历史渊源,同时,类似于现代性概念,也存在着后现代性、后现代化、后现代等术语的区别。这一概念最早在1870年出现在有关绘画风格的讨论之中(谢立中,2001b)。不过,相当一部分学者在承认后现代现象存在的同时,不认为存在所谓“后现代性”。前文所提及的哈贝马斯将现代性作为“一项未竟事业”的讨论明确反对“现代性已经终结”的观点,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系统地回顾了从黑格尔以来一直到福柯的主要哲学家围绕着现代性的讨论,并一一提出了批判,其最终的结论是必须迈向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交往行动理性(哈贝马斯,2004b)。而按照吉登斯等人的观点,所谓的后现代社会不过是现代社会的晚期,或者是高度发展的现代性。在谈到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概念时,吉登斯指出:“如果说我们正在进入后现代的阶段,那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的轨迹正在引导我们日益脱离现代性制度,并向一种新的不同的社会秩序转变。后现代主义,如果以一种有说服力的形式存在的话,可以说是对于这一转变的一种认识,但并不表明后现代性是存在的。”(吉登斯,2000:40)吉登斯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这一理论来分析这一社会秩序转变过程,类似观点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乌尔里希·贝克、斯科特·拉什等人。三人虽然对自反性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都对自反性的关键主题表达了同样的关心(贝克、吉登斯、拉什,2001:1)。在贝克看来,自反性首先是指“自我对抗”,而非反思。“‘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同上:5),在这种可能性的观照下,“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a radicalization of modernity),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同上:6)。拉什则更为清晰地表述了对“自反性现代化”的理解,他提出了三个理解角度:一是“自反性现代化是关于相对结构的一种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或‘能动作用’(agency)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理论”;二是关于自反性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拉什指出有必要清晰区分自波德莱尔至本雅明、阿多诺所形成对现代性的美学理解和自康德到涂尔干、哈贝马斯所形成认知传统;第三点在于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是个性化的一种强大纲领(贝克、吉登斯、拉什:140)。吉登斯则从个人心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高度现代化社会中,人们是如何面对风险社会,并构建生活政治(吉登斯,1998:240-270)。
(五)现代性的概念谱系图
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现代性概念的理解途径,笔者试图将有关现代性的理解用图1-1所示的关系路径加以展示。其中关于现代性来源的有关论述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

图1-1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的图示
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认为不存在后现代性,正是因为他们是从认知分析的传统去探究这一问题。由于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提出了现代性是自我关系的对象化,因而,在现代性内部就存在着如哈贝马斯所言的“自我更新的因子”,任何对现代性的批判都将被看成这种因子发生作用的结果,也就无所谓后现代性。而对于美学传统的现代性来说,历来偏重于从反抗角度理解现代性(至少认为现代性内部存在相互矛盾的内容),从这种角度去观察现代性,会很明显地发现人们的心态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作为一种混淆生活和艺术界限的倾向,它和早期启蒙阶段强调艺术与大众情趣分野的倾向截然不同,由此,可以把这种新的倾向称为后现代性。然而,这两种不同的传统似乎在一种更大的背景下正在逐步互相靠近,这样一种过程是和社会学关于行动和结构这一经典主题的变迁过程息息相关的。这种趋势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关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在融合了结构和行动者之后更多地转向个体;二是分析领域(相应地)转向日常生活。从吉登斯有关“生活政治”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苗头。这一点或许诚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指出,现代性的最重要的三个后果之一就是社会的个体化。
三 作为观念、心态和行动模式的现代性
虽然对现代性概念的描述如此众多,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术语学的考证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清除阅读的障碍,而学科间对概念的不同阐释帮助我们加深对现代性复杂内涵的理解。从以上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关于现代性概念的区分中可以发现不同学科关于现代性的理解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深刻联系。就哲学和美学而言,二者实际上在人的主体性和日常生活的此岸性上取得共鸣;而社会学关于日常生活的分析又与哲学的现象学转向不无关联。如果从社会学研究的传统出发考虑,现代性更多地和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紧密关联;毕竟社会学在19世纪60年代发轫于欧洲,从一开始,其所关注的问题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关于此前现代性问题的起源讨论更多地应该被看成一种语义学或者词源学的追溯。因而,我们在此明确本书所讨论的现代性概念特征。
现代性由在启蒙运动以后、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历史进程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所造成,它是个体—群体对种种社会变迁的感受和反应,是在对社会变迁不同程度的觉察和反思基础上所形成的观念、心态和行为模式。
从这样的概念出发,现代性将是一个融合了多个学科视角的综合概念,它既包括各种富于哲学色彩思想(如理性和自由主义观念)对人们的影响,也包括由于此岸情结高涨所带来的世俗化审美情结,还包括对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化感受。这样一种理解虽然显得较为宽泛,但还是很明确地将现代性与制度领域的变革以及认知领域的现代特点明确区隔,从而提供一种概念上的明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