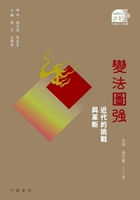
第5章 天朝危局 中國現代化之路向何方
引言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正處於清王朝統治的晚期,康乾盛世已為陳跡,朝廷腐敗,弊政叢生。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列強以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在內外交困、西學東漸的時代,不少有識之士痛定思痛,從制度和文化理念等層面探索強國禦侮之道。從經世致用到師夷長技,中國人的變法圖強,就此拉開帷幕。
前近代的中國與世界
一、前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以前中西之間較大規模的文化交流,始於十六世紀中葉,即明朝中後期。明清之際,隨着歐洲文明的崛起,天主教傳教士再度聯袂東來,且大多是耶穌會士,其中較為有名的有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利瑪竇(Matteo Ricci)、羅明堅(Michele Ruggleri)、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利瑪竇等人來華後,採取“合儒”策略,對中國傳統習俗持寬容態度。此外,他們還主動學習中國文化,並通過介紹西方科技、藝術等方式,博得中國皇帝與士大夫的好感,一度取得了較大的成功。
明末清初的來華耶穌會士,雖意在傳教,卻在不經意間成為了連通中西文化的使者。耶穌會士在把西方科學文化知識傳入中國的同時,也把一大批儒家經典以及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了歐洲。“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在此交相輝映,中西之間平等互惠、各取所需。在中國,隨着大量西方科學文化成果的引入,天文、曆法、數學、物理、醫學、哲學、地理、水利、建築、音樂、繪畫等傳統學問中出現了新的內涵,發生了新的變化。這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士大夫階層知識的增益、眼界的拓寬與觀念的轉變。在歐洲,十六至十八世紀出現了“中國文化熱”,對啟蒙運動產生了不容低估的影響。儒家無神論的哲學思想、德治主義的政治思想、融法律與道德為一體的倫理思想,以及重農輕商的經濟思想,尤為西方啟蒙思想家所關注。他們從中汲取養料,作為反神學、反封建、反專制的思想武器。雖然西方啟蒙思想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為我所用”式的功利性闡釋,或多或少是一種“誤讀”,但這種“誤讀”卻成為文明進步的必由之路,並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正因為如此,德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將這一時期的中西交流稱作是“一次互相的啟蒙”。
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並非完美無缺。來華耶穌會士出於神學的考量,對西方科學文化的介紹往往是有選擇性的。某些影響深遠的新成果,他們或鮮有提及,或語焉不詳。此外,此次文化交流的範圍與影響力也比較有限,局限在部分士大夫階層與傳教活動較為活躍的省份。清朝建立後,由於統治者實行“節取技能、禁傳學術”的政策,西學傳播的範圍更加狹窄,清朝皇帝對西學的掌控更加嚴密。至康熙時期,又爆發了“禮儀之爭”。一七〇四年,羅馬教皇發佈禁約,禁止中國教區的教徒敬天、祀孔、敬祖,他們派特使到中國晉見皇帝,並且採取了不為清朝統治者認可的禮儀規範。康熙聞之大為不悅,與教廷關係急劇惡化。一七一七年,清朝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此後歷代君王皆奉行禁教政策。一七七三年,教廷宣佈解散耶穌會,消息兩年後傳到中國,耶穌會宣告解散。此後,中西文化交流日趨衰落,幾近斷絕。隨着西方工業文明日漸成熟,西方人的文化自信也隨之增強,對外擴張的強度和速度超過以往。對中國來說,文化交流的中輟更為致命的是:中國失去了一次與西方平等交往、取長補短的時機,為近代的衰落留下了隱患。
二、清王朝的衰落與世界資本主義的勃興
十八世紀的中國,雖然經濟、文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現了“康乾盛世”的局面,但在乾隆末期已顯露出了衰敗的兆頭。嘉慶時期由盛轉衰,無論政治、經濟、文化都開始走下坡路,吏治腐敗、軍備廢弛、土地兼併十分嚴重。統治者厲行文化專制,大興文字獄,嚴重削弱了中國文化的生機與活力。老百姓走投無路,反清起事不斷發生。
清政府對內維持日益破敗的專制統治,對外則奉行閉關自守的政策。一方面嚴格限制中國人出海貿易或僑居國外,嚴格限制中國的糧食、鐵器、硫磺、絲茶和書籍等貨物出口,另一方面則嚴格限制來華的外國人的活動,防範外國人與中國人接觸。鴉片戰爭爆發前,中外貿易被嚴格限定在廣州一地,由清朝政府設立的公行管理外商。閉關政策不僅限制了中外貿易的蓬勃發展,還阻礙了中國科學文明的進步,也助長了統治者虛驕、守舊和盲目自大的惡習。總之,至十九世紀中葉,清王朝早已經失去了盛世的榮光。
清朝國力日益衰退的時候,又恰恰是西方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清軍入關前後,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逐漸確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爭先恐後地向海外進行殖民擴張。他們依靠海盜式掠奪、販賣奴隸、走私鴉片、發動殖民戰爭以及爭奪海上霸權等手段,從亞洲、非洲、美洲攫取了大量財富,擴大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其中,英國在十八世紀中葉開始進行工業革命,迅速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國家。隨着國內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為爭奪更多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英國加快了對外侵略擴張、開闢市場、建立殖民地的步伐。此時中國的東部、南部、西南部很多區域,正成為外國侵略勢力覬覦的目標。
可悲的是,統治中國的清王朝依然昧於世界形勢,做着“天朝上國”的迷夢。他們妄自尊大,認為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有。中國不需要依靠外國,西方卻離不開中國,外邦人皆是“夷狄蠻貊”,外邦遣使來華,是“輸誠向化”、“萬方來朝”,他們把“通商”看作為一種施予“蠻夷”的恩惠,是“懷柔遠人”的一種策略。在“天朝上國”觀念的支配下,清朝政府不僅對西方殖民者的擴張圖謀視而不見,而且對外交往時也斤斤計較於所謂的“禮儀問題”。一七九二年,英國以補賀乾隆八十壽辰為名,派遣以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為首的使團來華。次年九月在熱河覲見乾隆皇帝,他們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及天津為通商口岸,在京設立商館,劃舟山一島給英國做商業基地,在廣州附近設立供英商居住的地區(或允許英人在廣州“出入自便”),減免英貨在廣州和澳門之間的稅額等請求。乾隆皇帝向英王頒發“敕諭”,逐條予以駁斥,令馬戛爾尼乘興而來、掃興而去。一八一六年,英國又派遣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為首的使團來華,要求駐使北京、開放北方通商口岸,並爭取在廣州的英商擁有更大的自由等。該使團也由於覲見的禮儀問題,同清政府爭執不下而被趕了回去。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使團雖然無功而返,但絕不意味着中國是勝利者。然而清政府仍然因循舊有模式,對變化了的世界了解不多,也不願意去了解,從而決定了清政府此後在遭遇西方殖民者攻擊時陷入了懵懂與被動的境地。
三、鴉片走私與禁煙運動
所謂“鴉片戰爭”(Opium War),在英國也被稱為“第一次英中戰爭”(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戰爭”。儘管由於立場不同,人們對這場戰爭的命名與評判存在分歧,但戰爭與中英之間的貿易衝突、與英國非法的鴉片走私有着緊密的關聯,確實是毋庸置疑的。
從十八世紀後期開始,英國的毛織品、金屬製品、鐘錶、玻璃等商品湧入中國,中國的茶葉、生絲、土布和藥材輸入英國的數量也成倍增長。英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對象。然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是一個自然經濟佔主導地位的國家,人們的生活基本自給自足,對外國商品的需求量非常少。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一直處於出超的地位。以中英貿易來看,英國運到中國的商品,除了少量的毛織品、金屬製品和從印度轉販而來的棉花外,其他商品幾乎無人問津。貿易逆差使英國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為了解決貿易失衡的問題,英國政府先是派遣使節,希望中國能夠取消閉關政策,此後又於一八三四年結束了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壟斷特權,直接派遣駐華商務監督代表政府同清朝政府談判,還試圖增加煤炭、銅、鋼鐵、麻布、斜紋布等商品種類。然而,這一切均未能改變中英貿易的基本格局和走向。
既然和平合法的手段不能獲得預想的效果,為改變這種局面,牟取實際利益,英國開始把目光盯在鴉片走私上面。十九世紀後,英國開始將大量的鴉片自印度殖民地輸入中國,甚至不惜花費重金收買清朝官吏、勾結中國煙販,在中國建立販毒網絡。由於對華輸入鴉片的數量不斷增加,到鴉片戰爭前夕,英國在對華貿易中已由入超變為出超。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被打破,白銀大量外流,引起了一連串的社會惡果:銀貴錢賤,國內銀錢比價變動頻繁,加劇了人民的賦稅負擔,生活也愈發貧困。隨着各省拖欠的稅款日益增多,清政府出現了財政危機。此外,鴉片的泛濫,毒害了中國人的身心健康,加劇了民族危機。
圍繞鴉片問題,清政府內部出現了嚴重分歧,形成了以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太常寺卿許乃濟等人為代表的馳禁派和以鴻臚寺卿黃爵滋、湖廣總督林則徐為代表的嚴禁派。雙方爭論不已,最終嚴禁派佔了上風,獲得了道光皇帝的支持。一八三八年十月,道光皇帝下令各省認真查禁鴉片。轉年六月,清政府制訂《查禁鴉片章程》,禁煙運動在遼寧、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蘇、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新疆等地逐漸興起,其中,尤以林則徐在廣東地區的禁煙運動引人注目。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福建侯官人,字元撫,一字少穆,嘉慶進士。一八三八年九月,他上奏道光皇帝,贊成重治鴉片吸食者,強調“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十二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節制廣東水師。翌年三月,林則徐到達廣州,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整頓海防、嚴拿煙販、懲處受賄賣放的水師官弁。與此同時,他對外國煙販也採取了嚴厲措施,責令外商將躉船上所存鴉片造具清冊,聽候收繳,並具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即沒收,人即正法。林則徐態度十分堅決地表示:“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
英國人不甘受制於人,千方百計地對抗和破壞林則徐的禁煙部署。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一面下令躉船逃離,一面抗議廣州設防,還命令英國軍艦進行戰爭準備,並企圖包庇煙販、阻止洋商交出鴉片。廣州民眾聞訊之後包圍了洋館,林則徐下令停止中英貿易,派兵監視洋館,斷絕廣州與澳門的交通,迫使英國人就範。英國煙販被迫繳出二萬餘箱鴉片。林則徐在虎門海灘銷燬了所有收繳來的鴉片,用了二十餘天才銷燬完畢。
鴉片戰爭及其後果
一、鴉片戰爭與不平等條約的訂立
一八三九年八月,林則徐在廣東收繳和銷燬鴉片的消息傳到了英國,引來一片對華宣戰的叫囂。十月,英國召開內閣會議,決計對華動武。外交大臣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明確表示:對付中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先揍它一頓,然後再做解釋”,主張立即調遣軍艦封鎖中國。陸軍大臣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也堅決主張對華採取軍事行動。於是,內閣會議做出了“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的決定。一八四〇年一月,道光皇帝命令林則徐斷絕中英一切貿易。二月,英國政府任命懿律(George Elliot)和義律作為同清政府交涉的正、副全權代表,並任命懿律為總司令。四月,英議會正式通過了發動侵華戰爭的決議案,派兵開赴中國。六月,懿律率領的“東方遠征軍”相繼從印度、開普敦等地到達中國廣東海面,封鎖珠江口,悍然發動戰爭。由於廣東水師的英勇抵抗,奮勇反擊,英軍無法侵佔廣東,只得分兵北上。八月,英軍闖入天津,向直隸總督琦善遞交照會,提出賠款、割地等要求,震動京師。投降派趁機攻擊林則徐,道光皇帝下令將林則徐革職,派直隸總督琦善接任。轉年一月,英軍乘虛而入,攻陷虎門炮台後,又將兵艦駛入珠江,進逼廣州,此後還繼續北犯,廈門、吳淞口、鎮江相繼失陷。軍事潰敗使得清朝政府慌亂不堪,被迫求和。一八四二年八月,耆英、伊里布奉命全權辦理對英交涉。兩人先後到達南京,開始與英國全權公使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談判。
八月二十九日,耆英、伊里布等人與璞鼎查在英艦“漢華麗”號上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主要內容有:割香港給英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賠償英國二千一百萬元;協定關稅,英國對華進口貨物繳納稅款,由中英雙方議定。一八四三年七月、十月,中英又相繼簽訂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英國又攫取了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英國人享有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建立租界,以及壓低關稅等多項特權。《南京條約》開啟了外國侵略者用不平等條約使對華侵略“合法化”的先例。此後歐美列強紛至沓來,紛紛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並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的規定相互援引,使中國喪失了更多的主權。《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和法國爭相效尤,一八四四年七月中美簽訂《望廈條約》,十月中法簽訂《黃埔條約》。美、法兩國除享有英人在《南京條約》中的全部特權外,還擴大了侵略特權。如《望廈條約》擴大了領事裁判權,規定中國人與美國人、美國人與其他外國人在華發生的一切訴訟,中國官員均不得過問;擴大了關稅協定權,規定中國要變更關稅稅則,必須取得美國的同意。中法《黃埔條約》不但攫取了英美所取得的全部特權,還獲得在通商口岸傳教以及清政府必須保護教堂和傳教士的特權。一八四六年二月,清政府被迫宣佈解除清初頒佈的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教的禁令。
二、鴉片戰爭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深遠影響
鴉片戰爭及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是中國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奴役的開始,也是中國社會、文化的重要轉折點。比對戰前、戰後的各種情況,變化尤其明顯。戰前,中國是領土完整和獨立自主的國家。戰後,中國不僅在政治上開始喪失獨立自主的地位,在經濟上也日益淪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附庸。外國人在五口地區傾銷商品、走私鴉片、掠奪原料、強佔租界、控制海關,加深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然而,鴉片戰爭帶給中國的影響,不只有破壞的一面,還有超出西方列強預料的另一面。隨着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入侵,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現代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口岸城市發展壯大。鴉片戰爭後,在各通商口岸,外國商人直接僱傭中國人充當居間人或代理人為其推銷商品和收購出口貨物,這些居間人或代理人成為中國近代買辦、民族資本家的前身。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碼頭工人和在外輪上工作的海員,以及船舶修造工人等。他們是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隨着買辦、民族資本家與產業工人群體逐漸形成,各自的文化和政治訴求紛紛出現,中國的社會結構更加複雜,蘊藏着巨大的變革潛能。
一八四五年,英國人在上海建立租界,是為西方列強在華設立租界之始。此後美、法兩國也分別在上海劃定租界,建立起一套殖民地管理制度,並推廣到其他通商口岸。最初,中國政府對租界內行政、司法還有干預權。後來,外國侵略者逐漸實行獨立於中國的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為“國中之國”,成為他們進行政治和經濟侵略的基地。然而,租界既是“侵略基地”,也是全面展示西方現代文明的櫥窗。以上海為例,“浦濱一帶,率皆西人舍宇”。機製棉紡織品、自鳴鐘、望遠鏡、顯微鏡、寒暑錶、火輪機器、照相術、西醫西藥、書館印廠、公園、學校、報刊雜誌乃至西洋節慶、新式婚禮,紛紛登陸滬上,深刻影響着當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觀念。透過口岸城市中的租界,中國人看到了傳統文化中的種種不足;租界裏散發出來的文明氣息,展現出來的各項成果,成為他們改變自己、改造國家的範本。
單就文化而言,鴉片戰爭還催生了近代中國西學東漸的又一次高潮。直到二十世紀初,外國傳教士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督教傳教士輸入西學的實踐活動,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初。一八〇七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飄洋過海來到中國,由於清政府厲行禁教和閉關政策,傳教活動難以在中國內陸地區展開。於是,在毗鄰中國的南洋一帶,如馬六甲、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新加坡等地,逐漸聚攏了一批西方傳教士。他們開學校、辦印刷所、出版書籍報刊,在華人中傳播西學。鴉片戰爭後,憑藉不平等條約的庇護,基督教會的文字、教育、醫療、慈善等項事工得以迅速擴展至中國沿海各主要通商口岸,在傳播西方現代科學、推廣新式教育、改良社會風俗、開展慈善事業等方面均做出了不少努力和貢獻,深刻影響着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及其走向。可以說,對於近代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基督教傳教士有拓荒和啟蒙之功。
從經世思潮到開眼看世界
一、傳統文化的自我調適與經世思潮的復興
十九世紀清王朝的衰落與鴉片戰爭的爆發,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儒家學說的內在格局也發生了某些變化,乾嘉時期曾盛極一時的漢學(即古文經學、樸學、考據學)逐漸沒落,理學、今文經學、經世之學再度復興。嘉道之際,隨着社會矛盾的激化,漢學泥古瑣碎、空疏無用、脫離現實的治學理念已無法應對嚴峻的、急劇變化的局面。一些關注國計民生且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家和開明官紳,開始大力呼籲重振清初“經世致用”的學風,反對脫離實際,注重研究現實問題,以求紓解民困、匡時濟世、安定民心。
經世思想古已有之,早在漢代就已經逐漸成為儒家文化的傳統之一。縱觀中國歷史,每當社會出現嚴重危機、亟待變革之時,往往是經世思想的活躍時期。一八二六年,賀長齡、魏源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問世,揭開了前近代經世思潮的序幕。該書凡一百四十卷,分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八類,類下又分子目,彙編了自清初至道光初年的官方文書、專著、述論、奏疏、書劄等文獻,共計二千二百三十六篇文章,出自七百零二人之手。《皇朝經世文編》出版後影響較大,曾多次翻印。道咸之際,歷經鴉片戰爭的刺激,經世思潮蔚然成風,成為這一時期的顯學。誠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所說:
“鴉片戰役”以後,志士扼腕切齒,引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還顧室中,則皆沉黑積穢。於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暗,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試奮鬥,於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於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
道咸之際的“經世”思潮,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批判現實、倡言變法;二是改革弊
政,研討漕運、海運、鹽法、河工、農事諸大政;三是探究邊疆、域外史地,用以禦敵保疆;四是纂修當代歷史。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阮元、李兆洛、陳壽祺、包世臣、陶澍、徐松、張穆、賀長齡、林則徐、姚瑩、周濟、龔自珍、黃爵滋、金應麟、魏源、陳慶鏞、徐繼畬、梁廷枏、沈垚、張際亮、夏燮、湯鵬、陳金城、吳嘉賓、魯一同、何秋濤、楊士達、林昌彝等。這些人士身份複雜,上有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下有寄人籬下的幕僚;其學術背景與具體主張多有不同,但大體秉持經世務實、救世濟民的治學理念,這也體現出了經世思潮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廣泛的文化基礎。
經世之學有着強勁的生命力。自《皇朝經世文編》問世後,續編之作層出不窮,到一九一三年的《民國經世文編》為止,竟達二十種之多。儘管經世致用思想在本質上仍屬於“舊學”的範疇,其對傳統文化的繼承、批判與變革,對西學的理解與採納等方面有着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在國門初開、西學尚未被廣泛接受的轉型時期,經世思想顯然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正是在經世之學“務實”、“求變”理念的指引下,有識之士開始直面危機,了解世界、接納西學。經世思潮對近代“新學”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二、面向西方:開眼看世界的先驅
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和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化,促使一部分開明官員和士紳改變了之前閉目塞聽和妄自尊大的態度,提出了認識西方、學習西方和抵禦外侮的新觀點。許多志士仁人積極探求西方的科學知識,研究外國的歷史和地理知識,介紹西方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逐漸形成了認識西方、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出現了一批具有重大啟蒙作用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據統計,一八四一至一八六一年間,中國人至少編寫了二十二部介紹世界各地情況的著作,涉及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科技、歷史、地理、文化、教育、宗教等各方面。
1.林則徐: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則徐被譽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早在鴉片戰爭期間,出於禁煙的需要,他已開始設法了解夷情,並組織人員編譯西方書刊。新聞、歷史、地理、經濟、法律、軍事、科技、文化、對華評論等,均在其搜求編譯之列。由他主持編譯的文獻主要有《華事夷言》、《澳門新聞紙》、《澳門月報》、《各國律例》、《四洲志》等等,其中《四洲志》的影響最大。《四洲志》依據英國人慕瑞所編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譯而成,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簡明扼要地敍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個國家的地理、歷史和政情,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相對完整、系統的世界地理志書。此後,林則徐將《四洲志》抄本及有關資料轉交好友魏源,為魏源編著《海國圖志》提供了不少便利。
2.魏源與《海國圖志》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字默深,湖南邵陽人。一八四一年他進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鴉片戰爭時期參與了浙東的抗英戰爭。作為戰爭的親歷者,魏源親眼目睹了清朝政府在戰爭中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是年,他接受了林則徐的囑託,在《四洲志》的基礎上增補大量資料,於次年十二月編成《海國圖志》五十卷。一八四七年,他將該書的內容擴充到六十卷,一八五二年又增加至一百卷。
作為近代中國人編撰的一部世界史地著作,該書主要根據林則徐的《四洲志》、中國歷代史志以及明末至鴉片戰爭時期西人所寫的世界歷史地理著作、地圖、部分科技資料勾稽貫串而成。正如魏源本人所言,與以往域外史地著作“皆以中土人譚西洋”不同,吸收了西人著述成果的《海國圖志》是在努力“以西洋人譚西洋”。
魏源在序言中闡釋了編纂《海國圖志》的目的:“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為達到此目的,魏源將總結鴉片戰爭教訓、論述海防戰略戰術的《籌海篇》作為開篇,置於各卷之首。之後重點介紹了五大洲數十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情況,末尾尚有《國地總論》、《夷情備采》以及關於仿造西洋船炮及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的《西方器藝雜述》數卷。百卷本《海國圖志》約有八十八萬字,並有各種地圖七十五幅,西洋船、炮、器藝等圖式四十二頁,可謂是當時內容最豐富的有關世界知識和海防的百科全書。
3.梁廷枏與《海國四說》
梁廷枏(一七九六—一八六一),字章冉,號藤花亭主人,廣東順德人,歷任廣東海防書局纂修,越華、粵秀書院監院,學海堂學長等,鴉片戰爭時期,他曾大力協助林則徐謀劃禁煙、海防等事。他平生勤於治學,著有《廣東海防彙覽》、《粵海關志》、《海國四說》等。
《海國四說》是最能代表梁廷枏“籌海防夷”思想的作品,由《合省國說》、《蘭侖偶說》、《粵道貢國說》和《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四部著作構成,一八四四年陸續寫成,一八四六年結集刊行。“合省國”即美利堅合眾國,“蘭侖”即英國首都倫敦,泛指英國。《合省國說》三卷,是中國人編寫的第一部系統的美國通志,對美國政治制度的介紹尤為詳盡;《蘭侖偶說》四卷,由梁氏《英吉利國記》擴充而成,介紹了英國千餘年的歷史、風俗及各種制度,並述及中英貿易與鴉片問題;《粵道貢國說》六卷,涉及暹羅、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意大利、英國等國家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及各“貢國”的歷史、風情、民俗等,實為前近代中西貿易資料長編;《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則介紹了基督教的教義、教規、教史及其傳入中國的歷史,並探究了其不能取代儒學的原因。該書也是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優秀域外史地研究著作之一。
4.徐繼畬與《瀛寰志略》
徐繼畬(一七九五—一八七三),字健男,號松龕,山西代州五台縣人。道光進士,鴉片戰爭前後,他擔任福建延津紹道、兼署汀漳龍道道台,後任廣東巡按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撫等職,親自參與了廈門防禦戰和戰後福建地區的通商事務。在與來華西方人的密切交往中,他開始細心收集、研究域外新知,撰寫研究著作。一八四八年,幾經修改增補,《瀛寰志略》終於問世。
《瀛寰志略》全書共分十卷,卷一先列地球兩半球圖,述地球概況,五大洲、五大洋情況,後為《皇清一統輿地圖》與亞洲情況;卷二、卷三續述亞洲;卷四至卷七述歐洲;卷八述非洲;卷九、卷十述美洲。與同時代其他世界地理著述不同,《瀛寰志略》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專著,而非資料彙編。由於徐繼畬在研究過程中直接獲得了一些西方傳教士與外交官的幫助,並盡心考證,力求準確,該書質量上乘。據美國學者龍夫威(Fred Drake)考證,與徐繼畬有過密切往來的西方人,除了美國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之外,還有英國駐廈門領事記里布(Henry Gribble),美國傳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坎明(William H. Cumming)、合文(James C. Hepburn),兩任英國駐福州領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以及英國香港總督德庇時(John Davis)等人。
徐繼畬在書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介紹歐洲和北美各國,每個歐洲國家的面積、人口、財稅、陸海軍規模都有具體的數字,對中國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都有記述。在敍述南洋、印度等有關史實時,他還詳細介紹了這些國家和島嶼淪為西方殖民地的過程。此外,徐繼畬還對歐美民主政治制度作了比較系統的介紹,並給予稱讚。對西方列強,他並未採用朝野慣用的“夷”字,而是換以“泰西”之名。這在當時也算是對傳統華夷觀念的一種超越。鑒於其傑出的學術貢獻,龍夫威稱讚徐繼畬是“東方的伽利略”。
三、近代條約口岸知識分子群體的崛起
除了林則徐等開明官紳,這一時期在通商口岸城市中還聚集了一群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對西方科技書籍的譯介亦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就是所謂的“條約口岸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treayport cities)。這一概念由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首創,係指生活在最早開埠的通商口岸、與西方文化發生密切接觸且在中外文化關係的思考方面有所心得的中國士人。在近代中國意義深遠的思想文化變革中,這些人也扮演了前驅者的角色。
鴉片戰爭後,開埠的上海逐漸成為西學輸入中國的重鎮之一。不少傳教士與中國文人匯集於此,彼此合作,共同繁榮着中國近代文化、出版事業。如一八四三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創辦的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不僅是近代中國境內第一家機械印刷所,而且還是一所中西人士共事的出版機構。該館在一八四三年由麥都思將巴達維亞印刷所的設備遷至上海組建而成,早期主要印刷出版《聖經》及其他宗教書刊,自十九世紀中葉起開始增加對西學書籍的編譯出版。在墨海書館工作過的西方傳教士,主要有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等等,中國人則有王韜(一八二八—一八九七)、李善蘭(一八一一—一八八二)、張福僖(?—一八六二)、管嗣復(?—一八六〇)等。而王韜、李善蘭、張福僖、管嗣復等人,就是十分典型的條約口岸知識分子。
王韜,初名王利賓,字紫詮,號仲弢,江蘇蘇州人。一八四九年他來到上海,進入墨海書館工作,協助傳教士進行翻譯工作,起初主要幫助麥都思翻譯《聖經》。由於王韜文學素養深厚,《聖經》翻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外,王韜也翻譯了不少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的書籍,主要有《格致新學提綱》、《華英通商事略》、《重學淺說》、《光學圖說》和《西國天學源流》等。王韜在編譯西學書籍之餘,還細心考究西學,編成了《西學原始考》、《西學圖說》和《泰西著述考》等書,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西方的科學知識。同治年間,王韜遊歷西方諸國,逐漸成長為早期維新思想家。
李善蘭,字壬叔,號秋紉,浙江海寧人,近代著名科學家,在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等領域皆有成就。一八五二年,李善蘭進入墨海書館。因他在數學領域已有不少成就,所以受到偉烈亞力的器重。八年間,他協助西方傳教士翻譯了《幾何原本》(後九卷)、《幾何原本圓錐曲線說》、《重學》、《談天》、《代數學》、《代微積拾級》、《植物學》、《數理》等多部自然科學書籍。他所創造的一系列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名詞,如代數、未知數、函數、單項式、多項式、微積分、係數、常數、變數、分力、合力、植物學、細胞、光行差、月行差、視差等等,一直沿用至今。一八六九年,李善蘭出任京師同文館算學總教習。
張福僖,字南坪,浙江歸安人,近代著名天文學家,“精究小輪之理”。張福僖自幼酷愛天文曆算,對明清之際傳入中國的西學有所了解。一八五三年,他經好友李善蘭的介紹進入墨海書館工作。一八五三年,張福僖與艾約瑟合作翻譯了《光論》。《光論》是近代中國人翻譯的第一部西方光學著作。此外,張福僖還著有《彗星考略》、《日月交食考》等書。
管嗣復,字小異,江蘇南京人,桐城派大家管同之子,善詩文、通醫學。一八五四年他巧遇艾約瑟,隨其來到上海,進入墨海書館工作,與醫學傳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交好,二人合作翻譯了《西醫略論》、《婦嬰新說》、《內科新說》等醫學書籍。管嗣復也成為上海第一個兼通中醫和西醫的人。
由於此時的中國尚缺乏精通西方語言與學術的翻譯人才,而外國傳教士的中文水平亦無法獨立完成翻譯工作,上述譯著大多採取了“西譯中述”的形式,即由傳教士口譯,中國助手加以轉述和文字潤色。傳教士的中國助手們在譯介過程中,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學養與見識,在接受西學的過程中也展現出了一定的主動性。而這些譯著也為中國人了解西方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為日後中國人探索變法圖強之路奠定了基礎。
四、遲來的回應與錯失的機遇
鴉片戰爭後,儘管介紹世界地理與西方自然科學的書籍日漸增多,但這些書籍中所記述的新鮮事物並未得到時人的廣泛關注與認可,也沒有使中國社會產生顯著的變化。這由《海國圖志》與《灜寰志略》兩部書面世後的命運即可見一斑。《海國圖志》在付梓後的二十年中,並未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開來,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和民眾並不了解這部書。在有限的讀者中,對這部書和“師夷長技”的主張也都沒有重視,甚至反而予以否定。至於《灜寰志略》,更是招致保守人士的攻擊,徐繼畬本人也因此書而被罷官。
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人對這兩部書的評價才有所好轉。兩書受到洋務派與維新派人士的共同追捧。一八六五年,徐繼畬被清朝政府重新委以重任。已是古稀老人的他,先後任職於總理衙門和京師同文館。一八六七年,《灜寰志略》成為同文館的教科書,七十年代以後更成為中國出使外國人員的必備書。一八七九年,二十二歲的康有為遊覽香港,幡然醒悟,引發重新閱讀該書的興趣。他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寫道:“覽西人宮室之瓖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志》、《灜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而張之洞也在《勸學篇》中盛讚《海國圖志》為“中國知西政之始”。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海國圖志》與《灜寰志略》所傳達的知識觀念的理解和吸收,耗費了數十年的時光。
《海國圖志》與《灜寰志略》等書也曾流傳海外,包括近鄰日本,可日本人對這兩部書的回應比中國人快得多。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西方列強繼中國之後,又以武力叩開了日本的國門,強迫日本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就在此時,《海國圖志》傳入日本。日本維新志士如獲至寶,大力翻譯、註解、刊刻該書。僅一八五四至一八五六年間,《海國圖志》翻刻版本就多達二十二種。該書成為幕末日本了解西方列強的必備文獻,魏源的“師夷制夷”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接納,其對鴉片戰爭的總結與加強海防的建議,也被日本人批判性地加以吸收。此外,該書對日本幕末開國和維新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而《灜寰志略》最遲於一八六一年在日本出版,此後歷經翻刻,其版本和裝幀質量皆優於中國版本。該書深受日本人的喜愛,對其維新改革也起到了積極作用。正所謂“牆內開花牆外香”,《海國圖志》與《灜寰志略》在中日兩國的不同命運,仿佛也昭示着未來中國與日本國勢的不同走向。
至於那些近代條約口岸知識分子,他們此時也遊走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在精神上飽受煎熬。一方面,他們生活與工作的環境有助於深切體驗西方文化的精髓,養成憂患與改革意識。然而就民族情感而言,他們的內心也時常懷有一種恥辱感:“賣身事夷”、“附腥慕膻”,不僅有傷民族自尊,還會背負沉重的輿論壓力,被保守人士斥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他們一方面要與洋人、西學及西教為伍,一方面又受到傳統儒家思想的長期浸淫,對後者戀戀不捨。王韜在墨海書館的工作經歷,對他個人而言,絕非是一段美好的回憶。他之所以來到墨海書館工作,純粹是為生計所迫。儘管出色地完成了《聖經》的翻譯工作,但他內心卻根本不喜歡這種文字翻譯和潤飾工作。他甚至覺得文字潤飾工作毫無價值,也沒有任何樂趣,是對個人才能的嚴重浪費。他雖然接受了基督教洗禮,也參加教會的活動,對基督教學說卻不以為然,也無法接受西方的某些觀念和制度。
因此,這些條約口岸知識分子大多不會長期與洋人共事,如果有機會,便儘可能早地離開。王韜詳細記下了他的同事們接連離開墨海書館的情形:周雙庚“與慕君傭書,僅月餘即分手”;華蘅芳於一八五七年“適館三月而去”;張福禧因“徐君青中丞開府吳中,徵之至幕下”;管嗣復於一八五九年離開上海,“應懷什橋太守聘,往客山陰”。可見中國人與洋人共事是一件多麼尷尬、無奈而痛苦的事。與西人有過深入了解與交往的口岸知識分子尚且如此,就不用說那些守舊的官紳,以及恪守傳統的普通民眾了。
總而言之,鴉片戰爭後,儘管形勢突變,部分志士仁人已開始了變法圖強的思想與行為,然而戰爭並沒能使大多數中國人警醒,而這也造成了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遲滯。正如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蔣廷黻所說:“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豐末年,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然後有少數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機遇稍縱即逝,一去不返。事後證明,中國注定要為這虛擲的二十年光陰付出更多、更慘重的代價。在傳統文化的束縛下,中國人的變法圖強之路決不會一帆風順,注定是步履維艱、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