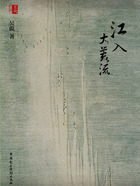
第一章 湛湛长江
长江万里之流,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波澜壮阔,浩瀚莫测。而地势最为险峻、四季风光最为雄奇者,当属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一段,即世人所谓“三峡”——夏季时,江水上涨,漫上山陵,沿溯阻绝。若是顺江而下,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相距一千二百里,即便疾风快马,也比不上船速,此即唐代诗仙李白所吟:“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
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
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
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
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
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
——魏晋 阮籍《咏怀》
上古大禹治水,曾自岷山导江 ,此江即为长江
,此江即为长江 。
。
长江万里之流,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波澜壮阔,浩瀚莫测。而地势最为险峻、四季风光最为雄奇者,当属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一段,即世人所谓“三峡” ——
——
七百里山水纡曲,连绵不绝。两岸青山挺拔隽秀,林木高茂,重岩叠嶂,隐天蔽日,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
夏季时,江水上涨,漫上山陵,沿溯阻绝。若是顺江而下,朝发白帝 ,暮至江陵
,暮至江陵 ,其间相距一千二百里,即便疾风快马,也比不上船速。此即唐代诗仙李白所吟:“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其间相距一千二百里,即便疾风快马,也比不上船速。此即唐代诗仙李白所吟:“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春冬之时,处处可见绿水回旋于白色湍流中,而荡漾的碧波中,清晰地倒映着两岸景物。悬崖绝壁之上,多生怪柏,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更有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水透亮,树峥嵘,山峻峭,草丰盛,趣味无穷。
秋天则最为特别。每至初晴或霜旦,林寒涧肃,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一派清凉寂静中,常有猿猴登高长啸,属引凄异。声音哀飒婉转,空谷传响,泠泠不绝。故而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虽有峡长谷深、奇峰突兀的极绝景致,然唐代之前,“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长久以来,竟没有人称赞三峡山水秀美,记录下来或口口相传的都是用登临此境令人恐惧来相诫。这自然是因为,滚滚江水被束缚于沟壑一般的峡谷后,兀然大变——
狂澜陡起,波涛汹涌,犹如万马奔腾。其间行船十分危险,不独水流湍急,且江中滩峡相间,稍有不慎,便会撞上暗礁。
譬如白帝城西面的瞿塘峡夔门处有一块黑色礁石,名滟滪堆,俗称燕窝石,又名犹豫石。此石夏季涨水时没于水中,秋季水落后方才现身,冬季则出水二十余丈,宛若庞然大物,昂然屹立于江心之中。如遇久旱水枯,滟滪露出大半,石下三足清晰可见,如一座硕大铜鼎。
这滟滪堆横江而立,拦截了几近半个航道,等于卡在了三峡咽喉,虽有“滟滪回澜”的磅礴景观——狂澜万卷,泡漩千重——却是天下至险之地,古来撞毁于此石之舟船不计其数,故有“生死关”之外号,令舟人行者望而生畏 。
。
传闻滟滪礁石下有夔龙 ,夏日水涨时,夔龙从支流梅溪河潜往龙潭沱,伏于龙王庙下,秋季水涸,又回滟滪
,夏日水涨时,夔龙从支流梅溪河潜往龙潭沱,伏于龙王庙下,秋季水涸,又回滟滪 。
。
不论夔龙传说是真是假,但邑人确实从滟滪随季没水总结出一套规律,以其为水候。有民谣唱道:“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幞,瞿塘不可触。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
此民谣描述的即是舟人利用滟滪堆来导航的情形。
举例而言,“滟滪大如象”,指冬季时水位下降,滟滪完全露出水面,宽大如象,横截江流,恰如唐诗圣杜甫在《滟滪堆》中所述:“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此时下水船可顺势而过。上水船则因水位过低,极易触礁,故而有“瞿塘不可上”之说。
而夏季山洪暴发,水位高涨,一江怒水奔泻而下,至滟滪堆时受到阻隔,遂化作白浪腾空而起,且形成千转百回的涡流,此即闻名遐迩的“滟滪回澜”。
只是这壮哉美景的背后,蕴藏着致命杀机。此时的滟滪堆,已大部没入水中,而顺水行船,则如快箭离弦,差之毫厘,便会发生船沉人亡的惨剧,故而“滟滪大如马”时,“瞿塘不可下”。当滟滪堆露出水面部分如牛、幞、龟、鳖一般大小时,更须加倍警惕。
而三峡之中,西陵峡才是最为险恶之处——航道曲折,滩多流急,两岸怪石横陈,江中暗礁林立,且峡中有峡,滩中有滩。滩险之处,水流如沸,泡漩翻滚,汹涌激荡,惊险万状,令人胆颤心寒。
有歌谣唱道:“西陵峡中行节稠,滩滩都是鬼见愁。”
自古以来,西陵峡便是步步惊魂之地,三峡船夫为求得生存,世代在此处,以生命与险滩激流搏击。
然一出西陵峡、抵达硖州夷陵 之地,咆哮澎湃的的长江水骤然变得和缓,漫为平流——此亦即“夷陵”得名之来历:“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是为因独特地形而形成的一大奇景。唐代诗仙李白名句“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之地,咆哮澎湃的的长江水骤然变得和缓,漫为平流——此亦即“夷陵”得名之来历:“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是为因独特地形而形成的一大奇景。唐代诗仙李白名句“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即描述此情景。
即描述此情景。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知硖州 朱庆基于西陵峡出口南津关以南建至喜亭,并延请时任夷陵县令
朱庆基于西陵峡出口南津关以南建至喜亭,并延请时任夷陵县令 的大名士欧阳修
的大名士欧阳修 作记。欧阳修欣然撰《硖州至喜亭记》。一句“夫天下之大险至此而始平夷,以为行人之喜幸”,道出了“至喜”二字的来历——
作记。欧阳修欣然撰《硖州至喜亭记》。一句“夫天下之大险至此而始平夷,以为行人之喜幸”,道出了“至喜”二字的来历——
江出峡始漫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
船夫们九死一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顺利出峡,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自古均是景因文名,就连“地下天宫”西湖亦是因白居易诗文方才显扬四方,至喜亭也因欧阳修之记,而成为硖州胜境 。
。
此时此刻,正有三男一女立于至喜亭中。眼帘所映,堪称一幅春江绝景图——
风日清美,江平如席,白云清嶂,远近映带,宛如天然丹青。
年长男子大约二十余岁,服饰华丽,英姿挺拔,一副富贵公子派头。
其人姓孙名固,字允中,号和父。籍贯郑州管城 ,平日喜自称“管城和父”,其实是在开封长大,算是地地道道的东京人氏。
,平日喜自称“管城和父”,其实是在开封长大,算是地地道道的东京人氏。
孙固九岁时读《论语》,慨然道:“我能行此道。”自幼流露出不凡志向。当世名儒石介一见到少年时的孙固便啧啧称赞,称其有公辅之器,将来必为国家栋梁,孙固遂成为石介的得意门生。
只是孙氏既为京师巨富,家境优渥,孙固自幼养尊处优,养成了倜傥率性的性格,于功名并不十分热衷,其人迄今未曾参加科举考试,便是例证。
孙固父亲孙奇年青时因经商而奔波于全国各地,曾数次走水路出入蜀地,故而也多次途经硖州。但这却是孙固平生第一次来到夷陵,凝睇大江浩荡东去,一时心潮澎湃,豪气大生,连日来的郁结情绪亦一扫而空。
孙固身侧的青衣男子姓苏名颂,字子容,虽然看上去要老沉得多,实际上比孙固还稍微年轻几岁。
苏氏是闽南著名望族,据称是汉代名臣苏武后裔。苏颂父亲苏绅更是本朝翰林学士加知制诰,博学多智,深受仁宗皇帝倚重。
受家风熏陶,苏颂自幼勤奋好学,成人后,对于经史九流、百家之说,乃至于算法、地志、山经、本草、训诂、律吕等学无所不通,年纪轻轻,便已是名满京城的大才子。他于本科蟾宫折桂 ,且在不久前娶屯田员外郎
,且在不久前娶屯田员外郎 凌景阳之女为妻
凌景阳之女为妻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可谓双喜临门。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可谓双喜临门。
中进士后,苏颂即正式步入仕途,被授为宿州观察推官 ,之所以临时告假、未立即走马上任,而是辗转随好友孙固来到硖州,自有一番不足为外人道之原委。
,之所以临时告假、未立即走马上任,而是辗转随好友孙固来到硖州,自有一番不足为外人道之原委。
苏颂左侧立着一名碧衣少女,明媚天真,笑意盈盈。
她是硖州人氏,姓吴名邦缦。其父吴钟曜为夷陵本地乡绅,年青时曾赴京赶考、游学开封,与朝臣石延年及名儒石介交好,虽因某种缘由未能应试,当年离开京后亦再未涉入科举半步,但却与石介、石延年等老友保持了长久的友谊,多年来书信来往不断。
去年石延年因酗酒过重,而中年早卒。吴钟曜伤痛天妒英才,恸哭不已,亦因悲伤过度而一病不起,迄今不见好转。
孙固因恩师石介的缘故,久慕吴钟曜大名。此次他因私事来到夷陵,亟需本地人氏协助,故而提前写信联系了吴氏。吴钟曜因病久卧,遂派爱子吴邦绶出面迎客。两方在信中相约于夷陵至喜亭相见。今日刚好是约定之期,然不巧吴邦绶有事外出,便由姊姊吴邦缦代劳。
这吴邦缦名为姊姊,因自幼更得父亲宠爱,办事远不如弟弟吴邦绶干练老成。她到至喜亭附近时,先遇到一名年青男子,见对方东张西望,又多少带些汴京口音,便想当然地将其人当作了孙固,上前招呼。不想那男子只是慕名来游览夷陵的游客,这便是正立于至喜亭碑前的郭源明了。而郭源明本不是口舌伶俐之人,对方又连珠般嘘寒问暖,竟一时愣住,不知该如何应答。
正好此时正主孙固与好友苏颂联袂赶到。郭源明虽然也是来自京师开封,看谈吐气度亦是大家子弟,却与孙固、苏颂二人并不相识——汴京到底是天下一等一的大都市,将近百万人口,远非夷陵这等偏僻小城所能比拟——孙固立即将郭源明误作了吴邦绶,上前自我介绍。
真正负责迎客的吴邦缦这才会意弄错了对象。她为人开放豪爽,丝毫不以为意,还为自己不分青红皂白的似火热情以及孙固的误会而大笑一番。
闹了一番小小的乌龙后,四人遂一道来到至喜亭。孙固、苏颂一登临亭子,便为美景吸引,径直奔去围栏边,醉心于远眺江景。
郭源明却不似二人,先来到亭子旁侧的亭碑前,静静伫立,细细品鉴碑文。
亭碑上所刻,便是曾任夷陵县令 的大名士欧阳修所作《至喜亭记》。然书法却并非其人手笔,这并非由于欧阳修书法不佳
的大名士欧阳修所作《至喜亭记》。然书法却并非其人手笔,这并非由于欧阳修书法不佳 ,而是本地惯例,须得延请夷陵本地善书者书写。而这位善书者,便是乡绅吴钟曜,也就是吴邦缦的生父。
,而是本地惯例,须得延请夷陵本地善书者书写。而这位善书者,便是乡绅吴钟曜,也就是吴邦缦的生父。
吴邦缦须尽地主之谊,不得不陪同在孙固、苏颂旁侧,但她内心深处其实更得意其父吴钟曜之书法,因而对即刻关注到《至喜亭记》碑文的郭源明格外有好感,眼角余光不断瞟了过去。
郭源明默诵了一遍亭记,又举手往青石碑面上摩挲,这才忍不住叹道:“好文!好字!”
吴邦缦登时露出喜色,侧过头去,欲主动告知石碑书法即为父亲手笔,却还是有些不好意思,话到嘴边,又勉强改口道:“郭郎喜爱书法吗?那么一定要去三游洞看看。”
郭源明未及回答,苏颂先好奇问道:“三游洞?是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之三游吗?”
吴邦缦应道:“是。虽然都在西陵峡外,但三游洞位置更高,风光与至喜亭这边大不相同。洞中景色奇丽,被喻为‘幻境’,而且石壁之上,有许多才子士人留下的墨宝 。当然了,也包括白元三人。前夷陵县令欧阳修公也在那里题过字。”
。当然了,也包括白元三人。前夷陵县令欧阳修公也在那里题过字。”
又特意侧身,指着亭边石碑道:“这亭碑上的字,不是欧阳修公所书。”
孙固显然未意识到吴邦缦的弦外之音,只是漫应道:“我倒是听过三游洞之名,原来石洞内外也有摩崖 。嗯,一定要去看看。”
。嗯,一定要去看看。”
吴邦缦笑道:“那有什么难事!等绶弟到了,我们去那边白家酒肆找船夫雇船,直接去游览三游洞。不远,从芦林渡到张飞渡,也就半个时辰的水路。”
又道:“走陆路也行,现任查知州上任后在西陵山边修了一座通远桥,直通到下牢津。但你们京城来的人,肯定走不惯山路,还是水路更舒适。”
一边说着,一边望向郭源明,显然是期待他也加入到己方行列。
郭源明却恍若未闻,目光始终只在石碑上,似有所思。
苏颂扭头看了一眼,这才会意过来,忙走到石碑前,道:“是了,这一定是数年前欧阳修公贬任夷陵县令时所作的《至喜亭记》。”
吴邦缦瘪了瘪嘴,道:“什么叫贬任?好像我们夷陵是什么烟瘴蛮荒之地。”
苏颂见主人不快,亦觉得失言。他为人宽厚,正欲出声赔礼时,孙固走过来道:“苏颂没有说错,欧阳修公当时确实是贬官离京。”
顿了顿,又叹道:“不过夷陵真是个好地方,绿水青山,比我想象得还要好。”
吴邦缦闻言当即大悦,嫣然笑道:“夷陵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多呢。三峡就不说了,你们都听过。从这里乘船溯流而上,入西陵峡不远,便是归州,是屈子屈原和落雁美人王昭君 的故乡。”
的故乡。”
苏颂忙道:“这段我在书上读过,归州原称归乡,又名秭归,地名跟屈原有关。《水经注》引用袁山松《宜都山川记》言:‘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因名曰秭归。’”
吴邦缦笑道:“是了,秭归名称确是这般由来,想不到苏郎连这个都知道。秭归可是连我们夷陵都不如的穷乡僻壤呢。”
也不待苏颂回应,又自行介绍道:“归州地段还有个兵书宝剑峡。据说当年刘备兵败猇亭后,为日后报仇雪恨,令丞相诸葛亮设法在悬崖上存放了一卷兵书、一把宝剑。宝剑就是长剑,倒没什么,兵书则是铁卷,为诸葛亮毕生所学,堪称无价之宝,故而得名‘兵书宝剑峡’。”
孙固嗤了一声,忍不住插口道:“这只是当地牵强附会、以讹传讹的传说吧。”
吴邦缦忙道:“不是传说,是真有其事。”
那兵书宝剑峡属西陵峡,为峡中之峡,位于香溪到庙河之间,长约四公里。在峡谷北岸陡崖石缝中,有一块突出之物,似是一个匣子。据称匣子里面所盛,便是诸葛亮所著兵书。兵书匣之下,有上粗下尖之物,竖直指向江中,这便是世人所称宝剑了 。
。
而兵书宝剑斜对面的峡口悬岩下,还有一岩洞,肉眼可见洞内堆积有许多粮食,据说是诸葛亮当年屯粮的米仓,故而进一步支持了“兵书宝剑”一说。
至于诸葛亮如何能将兵书、宝剑放置到绝壁之上,那便是长于巧思的孔明之能了。对于发明出木牛流马 、孔明灯
、孔明灯 等,制造出诸葛连弩
等,制造出诸葛连弩 的神奇能人而言,或许根本不算难事。
的神奇能人而言,或许根本不算难事。
动机嘛,有许多种说法,奉刘备之命只是其一。还有一种说法是,诸葛亮想要激励后世,唯有有胆略、有勇气者,方能取到兵书宝剑。故而时人有诗吟诵道:“天上阴符定不同,山川终古傲英雄。奇书末许人间读,我驾云梯欲仰攻。”
还有一种说法是,世人对用兵如神的诸葛亮很是仰慕,总希望能习得其兵法。而诸葛亮用兵,素来是随机应变,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他认为不拘泥于书本方才是正道,为了不误后人,遂决定将他自己所写的兵书弃置于峡谷中。故而有诗云:“兵法在一心,兵书言总固。弃置大峡中,恐怕后人误。”
无论如何,相信“兵书宝剑”之说的人不在少数。千百年来,无数勇士前仆后继,试图取得那两件神物,却无一例外以失败而告终。
这番兵书宝剑的前因后果,吴邦缦已向多人讲述过。一口气说完,她不无得意地看着孙固、苏颂二人,显然是期待对方表态。
孙固出身优渥,从来都是鲜衣怒马、意气风发,不会迎合他人,若非遭逢大变,亦不会有此趟夷陵之行,脾性较之从前,已算是收敛了许多。他始终认为“兵书宝剑”仅是附会之谈,然既然主人兴致极高,不便当面拂逆,遂一言不发,算是以沉默表态。
苏颂微一踌躇,即道:“如此说来,兵书宝剑峡上的那柄宝剑,极可能是刘备自佩的蜀主剑了。”他这般说,显然是认可诸葛亮兵书宝剑一说了。
吴邦缦大喜过望,忙问道:“蜀主剑,那是什么?”
苏颂道:“是刘备建立蜀国后所铸的宝剑 ,非但意义重大,还是一柄削铁如泥的绝世好剑。据说其锋锐程度,不在昔日蔡伦所造尚方斩马剑之下。”
,非但意义重大,还是一柄削铁如泥的绝世好剑。据说其锋锐程度,不在昔日蔡伦所造尚方斩马剑之下。”
吴邦缦远远不及苏颂博学多闻,也不知道尚方斩马剑是什么,只好奇问道:“这么说,那柄剑很了不得了?”
苏颂点头道:“很了不得,可以说是蜀国的象征。”
吴邦缦又问道:“苏郎又如何知道兵书宝剑峡的那柄剑是刘备的蜀主剑,而不是诸葛亮自己的佩剑?”
苏颂答道:“当年蜀汉立国,一共铸了八柄剑,诸葛亮佩剑,是蜀主八剑之一。蜀汉灭亡后,八剑均下落不明,唯一有后话者,就是诸葛亮所佩章武剑,被唐平卢节度使李师古 所得。李师古得到此剑后,还改章武剑为师古剑。因而兵书宝剑峡上的宝剑,不可能是佩剑。”
所得。李师古得到此剑后,还改章武剑为师古剑。因而兵书宝剑峡上的宝剑,不可能是佩剑。”
吴邦缦愈发好奇,问道:“既然蜀主八剑都下落不明,苏郎又如何肯定兵书宝剑峡的宝剑是刘备所佩蜀主剑?”
苏颂笑道:“后主刘禅即位后,便立即开炉铸造了新剑镇苗剑,据传是因苗疆局势不稳而铸剑。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刘备蜀主剑已在猇亭之战后失去,后主不能继承蜀汉开国宝剑,不得不再铸新剑。虽然征战对阵时难免混乱,但以刘备身份而言,失去佩剑的可能性不太大。既然缦娘很肯定诸葛亮在三峡留下了兵书宝剑,那么那柄宝剑极可能就是刘备的蜀主剑。”
他生性温厚,又转头问好友道:“孙兄以为如何?”
孙固素知苏颂见闻广博,听了他关于蜀主剑的一番推测,略略有了些兴致,但仍然摇头道:“兵书宝剑终究只是本地传说而已,未必真有其事。”
顿了顿,又道:“不过我倒真想去兵书宝剑峡看看。”
吴邦缦忙道:“兵书宝剑峡虽然不远,但三峡中上行水路难行,得预先准备好,今日肯定来不及了。反正孙郎要在夷陵呆上一阵子,改日再安排吧。”
孙固点了点头,这才有了心思,仔细读了一遍亭碑碑文。
一旁苏颂笑道:“读了欧阳公这篇亭记,孙兄可有所联想?”
孙固道:“《四贤一不肖》。”
苏颂笑道:“正是《四贤一不肖》。”
吴邦缦问道:“《四贤一不肖》是什么?”
孙固笑道:“跟欧阳修公上次遭贬夷陵有些干系。当年欧阳修公贬任夷陵县令后,小苏连襟蔡襄写了五首诗,题名为《四贤一不肖》 ,本意是称颂贤者、痛斥奸邪,不想却传诵东京,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本意是称颂贤者、痛斥奸邪,不想却传诵东京,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吴邦缦忙问道:“这位蔡襄,应该就是孙郎上封信中提及的善品茗者吧?他跟苏郎是连襟吗?”
苏颂忙道:“不是。我娶的是凌景阳凌公之女凌氏。蔡襄兄所娶葛氏,是凌公外甥女,但凌公一向待之若亲女,所以亲朋好友偶尔也会戏称我与蔡襄兄是连襟。”
吴邦缦当即笑道:“原来不是外人。难怪绶弟上心得很,一早便出门了。”
原来蔡襄善于品茶 ,而孙氏酒肆茶庄遍布京师,蔡襄亦因此跟少主人孙固相识,结为好友。蔡襄曾读茶圣陆羽《茶经》
,而孙氏酒肆茶庄遍布京师,蔡襄亦因此跟少主人孙固相识,结为好友。蔡襄曾读茶圣陆羽《茶经》 及唐人李肇《国史补》
及唐人李肇《国史补》 。《茶经》中提到唐代产茶地,首列“山南”
。《茶经》中提到唐代产茶地,首列“山南” ,山南茶又以硖州为上,次襄州、荆州。陆羽还特别提到硖州茶生于远安、宜都、夷陵三县山谷,均为“石上英”,即产于山石之上的好茶。李肇《国史补》中亦列有硖州四大名茶碧涧、明月、芳蕊、茱萸寮,称均可与湖州紫笋
,山南茶又以硖州为上,次襄州、荆州。陆羽还特别提到硖州茶生于远安、宜都、夷陵三县山谷,均为“石上英”,即产于山石之上的好茶。李肇《国史补》中亦列有硖州四大名茶碧涧、明月、芳蕊、茱萸寮,称均可与湖州紫笋 相提并论。
相提并论。
然即便是专事茶业经营的孙氏,也从未见过硖州茶。蔡襄不免愈发好奇,听说孙固将来硖州,便一再请求他设法谋一些当地茶。
孙固料想夷陵一带山高水险,而当地能制出好茶的茶树多生长于山石之上,采摘困难,而朝廷茶政多变,大部分茶利入了朝廷及茶商腰包,茶农不乐冒险,才致硖州茶名渐没 。但又不能拂却好友的殷切期盼,便预先在写给吴氏的信中提了一句。吴邦绶既受父命招待远客,当然要全力以赴,今日一大早出门,便是去谋今春新野茶了。
。但又不能拂却好友的殷切期盼,便预先在写给吴氏的信中提了一句。吴邦绶既受父命招待远客,当然要全力以赴,今日一大早出门,便是去谋今春新野茶了。
孙固连忙道谢道:“我其实只是替蔡襄兄问上一句,没想到邦绶如此费心,实在有劳了。”
吴邦缦笑道:“这没什么,绶弟早跟采药人订好了,今日不过跑一趟腿取茶罢了。刚好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前一阵天天下雨,这几日晴了,正是采茶时节。”
又笑道:“那位凌景阳凌公,眼力可是好得很,所选女婿,尽为人中之杰。苏郎人才出众不说,那位蔡襄蔡郎,想必也是很了不起。”
这话本是夸赞之语,但从一名未婚少女口中说出来,便显得很是惊世骇俗。
孙固、苏颂二人久在京师,尚未见过如此大胆漫语的良家女子。二人交换一下眼色,心中均是一般想法:“这位缦娘,倒是有几分番邦女子的豪爽和气势。”
旋即想到夷陵西面长阳等地多土族巴人 ,多是劲悍忿决之辈,宋廷为此在硖州一地设有八寨
,多是劲悍忿决之辈,宋廷为此在硖州一地设有八寨 镇守弹压,料想夷陵虽是州治之地,却多少受了些蛮夷熏陶,导致风气如此,便也不以为意。
镇守弹压,料想夷陵虽是州治之地,却多少受了些蛮夷熏陶,导致风气如此,便也不以为意。
苏颂忙拱了拱手,笑道:“缦娘谬赞,实不敢当。哦,我是指关于苏某这句,蔡襄兄自然很了不起,诗文清妙,书法端庄,自成一体,还是品茶大家。”
吴邦缦笑道:“那位凌景阳凌公,难道当不起眼力好之赞吗?”
他三人围来亭碑时,郭源明已主动避让,自行走到栏杆之处,远眺江景,始终未参与三人对谈。但因为至喜亭并不大,三人也并非窃窃私语,言语还是能清晰传入耳中。吴邦缦问及苏颂岳父凌景阳时,郭源明忽而转过头来,古古怪怪地看了苏颂一眼。苏颂立时留意到了,便有些忸怩起来,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道:“嗯,这个嘛……”
吴邦缦见状纳罕不已,忙问道:“可是缦娘说错了话?”
孙固不忍好友难堪,遂插口道:“凌景阳不但是小苏岳父,还是我姑父。”
吴邦缦“呀”了一声,讶然道:“那你们……你二人也是亲眷了。”
孙固摇头道:“不是亲眷,只是朋友。”
又补充道:“我姑姑寡居多年,新近才与凌景阳成亲。”
吴邦缦奇道:“那他二位年纪……”
忽意识到失言,忙道:“抱歉,实在抱歉,我不该提这个的。”
孙固摆手道:“无妨。这桩婚姻其实是一桩丑事,早已轰传京师,不过夷陵地处偏僻,缦娘尚未听闻罢了。”特意转头,重重看了一眼郭源明,意指郭氏既来自京师,当早已听闻那桩“丑事”,所以适才才会以那样的目光看苏颂。
苏颂“咦”了一声,道:“这碑文书法不错。”
见落款题为“无为居士”,便问道:“这位无为居士是谁?”
吴邦缦总算等到了这句问话,正要报出无为居士是父亲吴钟曜自号,郭源明忽指着江面,失声问道:“快看,快看!那是什么?”
这自然是向地主吴邦缦发问了。吴邦缦忙赶至围栏边,却见江面上有一群青白色的大鱼正互相追逐嬉戏,不由得“呀”了一声,忙告道:“这是白鱀 ,俗称江猪子。”
,俗称江猪子。”
苏颂自幼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故而极为博学,闻言一愣,问道:“白鱀?何以我从未听过?”
吴邦缦道:“这是长江中独有的神物,轻易见不到的。”
又笑道:“恭喜几位了,今日见到了白鱀,便可以逢凶化吉,万事遂心如意。”
她不过随口一语,不想一直寡言少语的郭源明居然接话道:“承缦娘吉言,真希望会如此。”还双手合十,朝上举了举,似是在祈求上苍保佑。
吴邦缦笑道:“一定会的。”又道,“我们去白家酒肆吧,那里离江边近,看得更清楚。”
诸人包括郭源明在内,对这长江中的吉祥神物白鱀均有着浓厚的兴趣,便欣然出亭,随吴邦缦直朝白家酒肆而来。
孙固、苏颂此次来夷陵,也取传统路线,雇船走水路,对沿途风土人情已有大致了解——
一入楚地,即发现“满目皆茅茨”。民居多是茅草房屋,均是就地取材建造,墙为土坯或泥巴,壁厚而低矮,屋顶则用稻草或是麦秆、芦苇等长条状物来覆盖,四周延伸,令茅草下垂,以遮挡风雨。
一路行来,各地茅屋样式、风格也各有不同。江陵是荆湖北路治地所在,这一带的茅屋也盖得最好,“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许,整洁无一枝乱”。一些江陵民众靠种植柑橘致富,更是学富豪大户盖起了竹篱瓦屋。
而地处江陵上游的公安县 ,茅屋则更加精致可爱。至于夷陵,大概因为硖州一带相对偏僻贫瘠,茅屋也要破落得多,仅够勉强遮蔽风雨。
,茅屋则更加精致可爱。至于夷陵,大概因为硖州一带相对偏僻贫瘠,茅屋也要破落得多,仅够勉强遮蔽风雨。
长江沿岸休憩之所,如酒肆、茶寮等均为茅草房子,无一例外,唯独这白家酒肆是几间大瓦屋。苏颂至芦林渡下船时便已经望见,不免感到奇怪,此时既有本地人氏陪伴在侧,便忍不住问道:“那家白家酒肆……很厉害吗?”
吴邦缦笑道:“嗯,白家酒肆卖的是自家酿造的高粱酒,酒性很烈,一般人喝不了,主顾都是本地及来往的船夫。”
苏颂道:“我是说,硖州民房多是茅草房屋,何以这白家酒肆与众不同?”
吴邦缦“噢”了一声,笑道:“原来苏郎是指这个。白家酒肆这几间瓦屋很气派,对吧?说起来,也跟欧阳修公有些干系。”
硖州本地民居,除了富裕大户,基本都是茅草房子,即便是夷陵县城中的人家,也不例外。这种茅屋看着极具田园农家风情,其实问题很多——
所谓“茅屋年年破”,茅草房子使用寿命短,尤其是茅草屋顶,经不起长时间的风吹日晒雨打,需要经常翻修,否则便“年深损烂,不堪居住”。而一旦遇到阴雨连绵时,茅草久渍不干,极容易腐烂,再也难遮风雨,即形成所谓“漏屋”。
硖州一地四季分明,水热同季,寒旱同季。一到夏天,经常暴雨倾盆,“漏屋”随处可见,因而忙于修缮茅屋是家家户户的常态。而到了冬季,气候干燥,茅屋又极容易发生火灾。
数年前,欧阳修到夷陵任县令,一到地方,便立即留意到茅草房屋的诸多不便,于是建议上司硖州知州朱庆基鼓励民间改茅屋为瓦屋,既可让民众住得更舒适,也能有效避免火宅。朱庆基欣然接受,派人修缮城内城外道路,并进行了一系列民俗改革,如出榜号召百姓改建瓦房,官府还可以为改建者提供部分资助。
经过一番努力,夷陵面貌大有改观,不过主要还是集中在县城中。城外居民,有钱富户乡绅早已住着豪宅瓦房;穷苦者如山民等,即便有官府支持,也盖不起瓦屋。而那些以船为家的船夫,一向是朝不保夕,更不会加入盖房之列了。
再说白家酒肆。这家酒肆的原主是船夫三兄弟,名叫白谦、白泰、白吉。三兄弟原以摇橹打鱼为生,频繁出没于风波中,居无定所,只以船为家。后来老二白泰偶尔从一位雇主那里听到了酿酒之法,动了心思,便说服大哥、三弟放弃了白浪中求生存的日子,用辛苦积攒下来的钱,在芦林渡旁盖了三间茅屋,开了家酒肆,名“白家酒肆”。
当时硖州还没有至喜亭。白氏兄弟之所以选择此处,是因为芦林渡是出西陵峡的第一个大渡口。无论是溯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均要于此处停泊,要么为即将面临的三峡险途做好准备;要么为顺利渡过生死难关而庆幸,大大松口气。
白家酒肆开张后,果然生意奇好。只是白家所酿为高粱酒,不同于楚地传统醪酒,性子太烈,只有船夫才能接受。而那些船夫大多出身贫寒,手里也没几个钱,赊欠更是常有之事,白家酒肆自然也赚不了太多钱,故而酒卖得不错,但始终只是勉强维系存活。
后有扬州富商乘坐大船来到夷陵,适逢枯水季节,其船难以通过三峡险滩。富商又着急赶至蜀地,遂出重金聘请白氏兄弟驾船。
白氏明知此行凶险无比,但仍抵不住金钱诱惑,毕竟三兄弟都想着娶上媳妇儿成个家。于是老大白谦和老二白泰上了富商大船,留下老三白吉看家。
天有不测风云,这一趟果然不顺。富商大船在瞿塘峡撞上了滟滪堆,船毁人亡,包括富商及白谦、白泰在内的十三人,无一生还。留守酒肆的白吉悲恸异常,然受雇是你情我愿之事,白吉也无可奈何,只能继续独自经营白家酒肆。
那扬州富商有一名婢女紫烟,患了重病,经不起风浪折腾,富商便命她留在夷陵养病,并委托白吉照顾。主人出事后,紫烟就势嫁给了白吉,自此与丈夫一起经营酒肆。
那紫烟自幼被卖为婢女,紫烟只是供使唤的小名,不知原先姓氏,船夫们便随白姓,称她白娘。
白娘嫁给白吉后,虽然衣食上比从前要苦许多,但总算不再是低三下四的婢女身份,她倒更喜欢这样的日子。
只是上苍待白娘略有些薄情,不久后白吉即因离奇怪病过世,留下白娘孤身一人。她在辗转挣扎中生下一女,为白吉遗腹女。其名“秋练”,为路过孙姓富商所赠,取自唐代大诗人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诗句:“照室红炉簇曙花,萦窗素月垂文练。”因白女出生在秋季月夜,故得此名。
日子一天天过去,白娘成了白媪,白秋练也长大成人,成了远近闻名的美女。白家酒肆终于还是在风风雨雨中生存了下来,三间茅屋始终屹立未倒。这于孤儿寡母的白氏母女而言,是何等不易。
数年前,硖州知州朱庆基令州府出资,在芦林渡附近修建至喜亭。地方乡绅也联合起来,凑了一笔款子;甚至还有一名过路富商慷慨解囊,捐了两锭金子。
修完至喜亭,又修了周遭道路,还新辟了一条从至喜亭直通芦林渡的石阶路。
这一切忙完后,竟然还余下不少钱。夷陵县令欧阳修听闻白媪事迹后,怜悯相依为命的母女二人,又听说白家酒肆在三峡船夫中享有盛名,便向知州朱庆基建议将剩余款项拨给白家酒肆,用以改建房屋,既改善白氏母女处境,也能给过往船夫们一个更好的休憩之所。
朱庆基欣然应允,派人到白家酒肆告知后,却意外遭到白媪之女白秋练拒绝。白秋练认为白家酒肆当自食其力,不该平白无故接受官府资助。
然此刻消息已经传开,船夫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白氏母女实不能推却,只好同意。
建房时,船夫及乡邻们更是争相赶来帮忙,场面热烈,令人动容。
苏颂听完白家酒肆如何由茅屋变成了瓦房,当即笑道:“原来还有这样一番故事,这倒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孙固忽插口问道:“那位白秋练娘子多大年纪?”
吴邦缦道:“嗯,跟孙郎年纪差不多吧。她生得貌美,人又大方,上门提亲的人可多了。她因为要照顾母亲及酒肆,一直都不肯嫁人。”
孙固当即点了点头,又道:“她很了不起。”
到江边时,白家酒肆中歇脚的船夫亦已闻声而出,立于岸边,观看江心白鱀戏水。
吴邦缦忙引着众人过去。苏颂笑道:“这里视线果然更好。”
郭源明目力甚好,忽指着鱼群道:“那是什么?”
有船夫也发现了异常,惊叫道:“好像是个人。”
众人仔细看时,果见鱼群中有青色人形状物,因白鱀来回托引,便不得沉没入水。
一名船夫奇道:“怎么回事?”
他正要赶去渡口驾船前往江心察看,另一名船夫阻止道:“先别着急。”又回头叫道:“秋练娘子!秋练娘子!”
一名年青女子闻声而出。其人一身青衣,以青斑布帕首,甚是干练。这便是酒肆少主白秋练了,也算是夷陵本地的知名人物。
她一言不发地走到岸边,略略一望,便举手到嘴边,合成喇叭状,发出“咿咿呀呀”的类似婴儿的怪叫声。
孙固等人正感诧异时,江心那群白鱀竟然也开始“咿咿呀呀”地回应。原来这白秋练是在模仿白鱀的叫声。
最奇妙的是,那群白鱀随即便托着那青色人形状物往岸边而来。等到距离近了些,大致便可辨出那确实是个人,而且是名男子。
白秋练急忙叫了两名船夫,带着长杆步到岸下岩石处,等鱼群稍微接近,便举杆将青衣男子慢慢搭捞了过来。
白秋练又是一番“咿咿呀呀”,那群白鱀便争相翻越回应。白秋练又不断挥手,那群白鱀慢吞吞游回江心,又“咿呀”了一番,这才沉入水底。
孙固等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就连本地人吴邦缦也是第一次遇到,只看得目瞪口呆。
倒是苏颂最先反应过来,见船夫已将落水青衣男子抬上岸,平放在地上,忙赶过去道:“劳烦各位让让。在下略通医术,请让在下看看,或许这个人还有救。”
众船夫闻言,便避让了开去。苏颂生性古道热肠,也不忌讳什么,奔到那青衣男子边上,蹲下身来。只见对方面色铁青,双目紧闭,嘴唇惨白。再探鼻息,早已没了呼吸。
众船夫日日出入于风波之中,见惯生死,倒也不觉得意外。一名红脸船夫还弯下腰来,仔细看了看青衣男子面容,道:“这人好生面熟。”
另一名船夫则留意到异样,指着青衣男子胸腹问道:“这个人不是溺亡,是被凶器杀死的。”
苏颂于医术、药物均有所涉猎,当即点头道:“不错,这人胸腹被刺了两刀,而且两刀均在要害之处。落江之前,他应该就已经死了。”
白秋练皱紧眉头,问道:“他是谁?”
称“面熟”的红脸船夫道:“是那个……好像是那个……”“那个”了半天,也没说出名字来。
吴邦缦也大着胆子跟了过来,探身看了一眼青衣男子尸首,当即脸色大变。
孙固见她面色有异,不由一呆,问道:“难道他……他就是你弟弟邦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