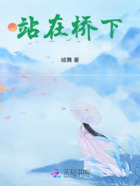
第4章 央视风暴
演播室的强光灯烤得乔夏后颈发烫。
她坐在《非遗中国》访谈席上,看着自己的脸在对面监视器里被分割成三个画面——左侧是昨天河滩质问的片段,中间是严松龄在机场被记者围堵的直播,右侧则是自己别在腰间的那枚子弹壳特写。
“乔小姐,您指控严教授与四十年前的污染事件有关,是否有确凿证据?“
主持人李晓雯的声音很温和,但乔夏注意到她耳返里不断闪烁的蓝光——那是后台导播在实时调整问题。玻璃墙外的制作人正疯狂比划着“切割“的手势。
乔夏端起茶杯。水面倒映出观众席最后一排的陌生面孔——穿黑色高领毛衣的男人正用手机拍摄全场,他指关节上的老茧明显是常年练琴留下的。
“证据在这里。“
她突然解开腰间绿丝绦,当众脱下外袍。现场一片哗然——内衬上缝着的七张显微照片在镜头下纤毫毕现,每张右下角都盖着红旗化工厂的检验章。
导播间乱成一团。
“切广告!快切——“
李晓雯的耳返突然炸响刺耳电流声。直播信号诡异地持续着,乔夏的声音通过卫星传向全国:
“1974年8月15日,黄河下游七个采样点同时检出氰化物超标,而当天在那里比武的七位民间武者......“
她举起奶奶的笔记本,翻到被血渍浸透的那页:
“除了我奶奶,其余六人的尸检报告都写着'溺水身亡'。“
监视器里的严松龄突然在机场暴怒,他推开记者时,西装袖口滑落——手腕内侧的齿轮刺青在镜头前一闪而过。
后台走廊的应急灯忽明忽暗。
乔夏被保安“护送“着走向出口时,那个黑衣男人正靠在消防柜旁摆弄手机。他抬头时,乔夏看清了他胸前的银色徽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双橄榄枝标志。
“周怀瑾。“他伸手挡住保安,“文化节组委会的。“
保安面面相觑。周怀瑾的拇指在手机屏幕上一划,乔夏的电子邀请函立刻跳出来,法国文化部的钢印在昏暗走廊里泛着微光。
“您刚才的表演......“他递来一件绣着暗纹的白色外套,“比独竹漂精彩十倍。“
乔夏闻到外套上淡淡的沉香味,袖口内衬用金线绣着《广陵散》的减字谱。
演播大楼外的露天咖啡座,周怀瑾用三枚铜钱在桌面排成卦象。
“严松龄提前飞巴黎不是逃跑。“他推过平板电脑,上面是会展中心地下三库的平面图,“第七个毒桶根本不在河里。“
乔夏盯着那个被标记为“1974年中法工业交流展品“的仓储区,突然明白奶奶当年为何坚持要她背《盐铁论》——“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
“他们当年往黄河排的只是实验废料。“周怀瑾的指尖停在某个加密区域,“真正的大规模生产......“
无人机的嗡鸣突然打断谈话。易天操纵的航拍器俯冲下来,吊篮里装着严松龄遗落在演播室的公文包。翻开的内袋露出半张泛黄的合影——年轻时的严松龄站在塞纳河畔,身旁的法国人捧着个刻有七星标记的金属桶。
深夜的高铁上,乔夏用毛笔在车窗上勾勒塞纳河岸线。
周怀瑾递来的资料显示,当年红旗化工厂的氰化物提纯技术,实际源自法国某军工企业。而奶奶他们取样的那天,恰逢中法签署首个工业合作协议。
“你奶奶的枪法叫'七星伴月'。“周怀瑾突然说,“七枪必须点在同一个呼吸周期。“
乔夏猛地转头。这套枪诀是乔家秘传,连易天都不知道。
月光透过车窗,在她掌心投下七个光斑。周怀瑾的怀表恰在此时打开,里面嵌着的照片上,年轻学者与一位白发武者并肩而立——那是穿着1973年全国运动会制服的奶奶。
“家父当年是水质监测员。“他轻声说,“也是第七个采样点的记录者。“
列车穿过隧道,黑暗吞没了两人震惊的表情。
巴黎戴高乐机场的电子屏正滚动播放严松龄的声明:
“某些网红为博关注污蔑学术前辈......“
乔夏拉高衣领。她腰间别着的已不是子弹壳,而是周怀瑾给的微型检测仪。安检门扫描到她时,仪器屏幕悄然亮起红色——航站楼某处有氰化物反应。
远处贵宾通道,严松龄正与接机的法国人握手。那人西装翻领上别着的,正是半个齿轮形状的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