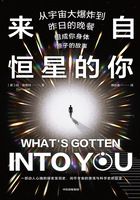
第5章 “真有趣”:肉眼永远看不见的东西
在科学界最激动人心的短语,预示着最多发现的短语,不是“我发现了”,而是“真有趣”。
——艾萨克·阿西莫夫,《归因》
可怜那些生活在有轨电车和马车时代的科学家,他们希望发现我们体内最基本的粒子,现在我们知道它们是从大爆炸中产生的。你要如何找到用肉眼甚至最强大的显微镜都无法看见的东西?这是一个长期困扰物理学家的难题。早在勒梅特和爱因斯坦钻研宇宙起源之前,就有人在探寻组成宇宙的最微小物质。然而,这项事业一直被疑云笼罩。他们真的有可能找到吗?古希腊人推测,万物甚至人类,都是由不可分割的微小单位组成的,他们称之为“atomos”,意为“微小且不可分割”。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许多化学家同意了这种说法,并称之为原子。但许多物理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1]颇具影响力的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称:“究其本质……原子和分子永远无法成为感官直面的对象。”[2]化学家的实验表明,原子在理论上存在,但从未有实验直接揭示过。当时没有科学家见过、触及过或测量过原子。
后来,两个不寻常的发现使怀疑者成了信仰者。1897年,在英国物理学的中心——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精明强干的J.J.汤姆孙正在研究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两个电极在玻璃真空管中通电时产生了神秘的阴极射线,它的本质是什么?出于好奇,他将射线暴露在磁场中,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他惊愕地发现,磁场使射线的路径发生了偏转。他出人意料地发现了看不见的带负电的粒子,我们现在知道它们是原子的一部分。1911年,乔治五世加冕为英国国王,海勒姆·宾厄姆探索了马丘比丘,汤姆孙已毕业的杰出学生欧内斯特·卢瑟福也有同样重大的发现。他朝一片薄薄的金箔发射了带正电的放射性粒子,大多数粒子如预期那样穿过金箔,但也有一些反弹了回来。他瞠目结舌。“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回忆道,“就好像你向一张薄纸发射了一枚15英寸[3]的炮弹,结果它反弹了回来。”这些粒子一定被金箔中密集的正电荷排斥了。他发现原子也含有带正电的原子核。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认可了卢瑟福的这一伟大结论:我们知道了我们最基本粒子的性质。宇宙中的一切都由原子构成。但希腊人错在认为这些粒子就是最小的。原子的中心是原子核,原子核的直径大约是原子直径的万分之一,原子核含有密集的带正电的粒子,后者被称为质子。汤姆孙发现的带负电的电子绕原子核在轨道上旋转,就像行星绕太阳旋转一样。[4]另外,原子的质量使卢瑟福怀疑原子核中还包含另一种物质:如今我们称为中子的不带电粒子。
没错,就是这样。没人有理由认为还会有更小的粒子存在。请注意,即使有人这么想,也没办法找到它们。当然,最强大的显微镜也无济于事。科学家用显微镜看见原子的概率和用肉眼看见冥王星的概率一样大。一个针头能装下数万亿个氢原子,而质子的直径是原子直径的十万分之一。[5]即便存在更小的粒子,我们似乎也永远不可能找到。
提醒一句:我们即将踏上一段旅程,深入探索我们周围一些最奇怪的现象。在找到最基本的粒子之前,物理学家会先发掘一个陈列室,里面摆满了一系列令人费解的亚原子粒子。但这条道路将崎岖而曲折,因为科学家最伟大的发现往往是在探寻截然不同的目标时取得的。
第一条意外线索将从澄澈的蓝天外出现。
1910年春,德国物理学家、耶稣会神父西奥多·武尔夫拿着一个面包盒大小的装置,从埃菲尔铁塔塔顶的电梯里走出来,他希望这个装置能解开一个令人挫败的谜团。烦人的电荷像忠诚的狗一样处处跟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将验电器(检测电荷的设备)造得极其灵敏,以至于仪器现在把他们逼得发疯。他们的验电器即使在完全绝缘的状态下也能检测到电荷。科学家把它们放在厚金属盒子里,隔离在水箱里,这些烦人的电荷仍然拒绝消失。[6]于是武尔夫设计了一种超级坚固的便携式验电器,而后出发,决心查明电荷的来源。
他最合情合理的猜想是放射性现象。就在10多年前,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亨利·贝可勒尔碰巧把铀盐放在书桌抽屉里的照相底板上。几天后,他震惊地发现这些盐在底板上产生了图像。他还发现一些岩石有放射性,比如铀,也就是说,它们会释放带电粒子,以及波长短于可见光的不可见电磁脉冲。因此,在武尔夫看来,空气中持续存在的电荷肯定是由地底深处的放射性岩石产生的。它们发出的辐射必然撞击了大气中的分子,释放电子,从而产生带电粒子。武尔夫带着他的验电器,降到洞穴深处去证明这一点。[7]他以为读数会随着他接近放射源头而升高。但它们没有。于是,他把验电器绑在背上,乘电梯登上当时世界最高的人造建筑——埃菲尔铁塔的顶端,指望电荷会消失。但它们没有——至少消失得不够多。留下的电荷还是太多。谜团更神秘了。
武尔夫的实验鼓舞了一位大胆的奥地利物理学家,28岁的维克托·赫斯接手了这项挑战。赫斯认为,想知道这些麻烦的电荷是否来自地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验电器带到更高的地方。在1911年,实现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冒险进行高空飞行——乘坐热气球。
在当地一家航空俱乐部的帮助下,赫斯在维也纳附近进行了6次飞行,高度达到了6000英尺。[8]他的实验没有定论(不过一次日食期间的实验证实了这些电荷并非来自太阳),这令人泄气。但他不会让小危险妨碍一个好的实验,于是决心飞得更高。他说服奥地利一个小镇上的德国气球爱好者协会自愿献出其飞行编队的骄傲:一个橙黑相间、12层楼高且技术最先进的美丽热气球,名为波希米亚。[9]
1912年8月7日的黎明时分,在一大片绿地上,航空俱乐部用马车拉来了气罐,为巨大的波希米亚充气。早晨6点12分,赫斯挤进一个小柳条篮里,身边还有一名驾驶员、一名气象观测员、一个小工作台、三台验电器、随身行李,以及最重要的三个大氧气瓶。[10]
空间很紧凑,但赫斯很清楚自己需要这些必要物资。在我们每一次呼吸吸入的氧气里,大脑要消耗其中的四分之一。如果氧气摄入不够,就会有麻烦。这个事实在30多年前就得到有力的证明,当时,有三名法国热气球驾驶员搭乘一只名为天顶的热气球,试图打破飞行高度纪录。他们随身携带了氧气,这很明智;但他们没有吸入足够的氧气,这很愚蠢。其中一人回忆,在超过20000英尺后,“内心的喜悦就像周围天光的映照。人变得很无所谓”[11]。他感到“呆若木鸡”,他的舌头麻痹了。然后他昏厥了。下降时,他苏醒过来,却发现同伴们都耷拉着身体。缺氧迅速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他成了唯一的幸存者。他们可怕的死亡记录使热气球驾驶员将高空飞行推后了20年,而赫斯计划爬升到几乎同样的高度,不过他打算活下去。
早上7点,他开始上升,带他升空的是氢气(正是这种爆炸性气体后来毁灭了德国齐柏林飞艇“兴登堡号”)。他们升到了万里无云的晴空。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发现自己飘过德国边境。在13000英尺的高空,他们遭遇了时速30英里[12]的狂风。赫斯裹紧大衣,不顾刺骨的严寒,勇敢地继续测量。到了9点15分,他累了。他理智地决定是时候吸点氧气了。一个小时后,他们又上升了3英里,在令人眩晕的17400英尺高空,他如此虚弱,担心自己会晕倒,于是决定该停止工作了。他命令机长释放热气球中的一些氢气。到了13000英尺的高度,他开始恢复知觉。
再次踏上草场坚实的地面,赫斯兴高采烈。升到最高处时,他测量到的电荷是地面上的两倍。这只可能有一种解释——他升得越高,就越接近电荷的源头。他确信自己的发现:一股来自外太空的电荷在持续轰击地球。
其他物理学家难以接受这项发现。比如说,难道赫斯的仪器不更有可能受到极低温度的影响?[13]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就极其激烈地反对它,然而到了1925年,他自己的实验证实了赫斯的测量结果。[14]它们很快被称为密立根射线,但遭到了赫斯的强烈反对,于是另一个源自密立根的名称被迫保留——宇宙射线。[15]
这令人遗憾,因为它们和密立根设想的不同,并不是一种像光、放射性射线或X射线那样有独特波长的电磁辐射。相反,宇宙射线是带电粒子和光子流,持续不断地落在我们身上。
当时的物理学家还不知道,这些看不见的倾盆大雨中含有更小粒子的提示。只有等他们发明出新工具来“看见”小得不可思议的东西后,才能找到它们。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J.J.汤姆孙手下的一位研究人员就发明了一种这样的工具,但这位痴迷云的年轻人发明它的目的与上述目标大相径庭。查尔斯·汤姆孙·里斯·威尔逊是一位苏格兰牧羊人的儿子,他身材高大,性格文静,说话温和。1895年,这位年轻人刚从剑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位,便自愿到一个简陋的气象观测站工作数周。它位于苏格兰最高峰本内维斯山。他睡觉的小石屋经常被大雾浸透,或被雷雨折磨。但在清晨,他偶尔会看见绚丽的景象。在脚下的云海上,他看到了那样壮美的彩虹光晕,便决定在实验室里制造人造云来研究。
可能是因为有明显的口吃,威尔逊耐心非凡,一回到剑桥大学,他就自学了精妙绝伦的玻璃吹制技术。经历了无数次破损后,他建造了一个精巧的玻璃腔室,它有一个可以改变内部压力的活塞。经过周密的实验,威尔逊兴奋地发现,如果他在腔室里充满潮湿的空气,然后利用活塞迅速扩大其体积,水蒸气就会凝结在空气中的尘粒上。他制造出了人造云。
接着,德国的一项发现使他的研究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项使他那不起眼的台上器具变成一种工具的发现,连欧内斯特·卢瑟福都称赞这种工具为“科学史上最独创且奇妙之仪器”[16]。
在300英里外的维尔茨堡大学,物理学家威廉·伦琴和J.J.汤姆孙一样,正在研究阴极射线管产生的射线。他用黑色纸板仔细盖住玻璃管,以防光线漏出,但他碰巧瞥见附近一面涂有磷光漆的屏幕,吃惊地发现它在发光,就像被看不见的光线照亮了一般。他震惊不已。
他担心别人会认为他疯了,便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开始昼夜不停地调查。[17]他让他信任的妻子把手放在玻璃管和照相底板之间,上面显现了她的指骨和结婚戒指的幽灵般影像。她看着影像说:“我看到了我的死亡。”伦琴发现,当阴极射线管内的阴极射线击中管子末端时,会发射出完全不同的东西。[18]他与X射线不期而遇,它是波长比可见光短得多的电磁波,只能被重元素吸收,比如我们骨骼中的钙。
回到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这里的物理学家对报纸上透视射线相关的报道持怀疑态度,直到他们看到了照片。在谈到此时扎堆研究它们的物理学家时,改变了想法的卢瑟福写道:“欧洲几乎每一位教授都在摩拳擦掌。”[19]很快,美国的托马斯·爱迪生动起了X射线的脑筋,开始研制X射线灯泡。(数年后,他的助手被X射线灼伤,死于癌症,他放弃了这些尝试。)
查尔斯·威尔逊怀着满腔热情加入了研究行列。凭着直觉,他向J.J.汤姆孙借了一根简易的阴极管,朝充满潮湿空气的云室发射了X射线。他吃惊地看到X射线在腔室里制造了浓雾。[20]它们从空气分子中电离电子,产生了被称为离子的带电分子,水蒸气凝结在上面,形成了雾滴。威尔逊欣喜若狂。[21]他的云室揭示了不可见粒子的踪迹:这些粒子个体如此之小,以至于没有人想象它们能被探测到。当他把放射性粒子引入他的云室时,“小缕云絮”如飞机后面的蒸汽尾迹一样近乎神奇地出现又消失。[22]这近乎魔法。威尔逊煞费苦心地改进了云室,他发明的用来研究云的简单仪器很快成为世界广泛使用的强大工具,用以研究电子、离子和放射性粒子。但是他的云室还未实现其最伟大的成就——探测比原子还小的未知粒子。
到了1932年,科学家已经确定宇宙射线中含有电子,因此加州理工学院一位名叫卡尔·安德森的年轻研究员不情愿地建造了一个云室来研究它们。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安德森想转到另一所大学,但他的导师坚持让他先做这个项目,这位导师恰好是罗伯特·密立根,也就是证实赫斯发现的宇宙射线存在的密立根。[23]安德森从南方爱迪生公司的一个废品场借来一些元件,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电磁铁,它的电磁强度足以使从天空飞进云室的任何电子的路径偏转。他的耐心有时会得到回报,他成功拍摄到了电子在强电磁场中偏转的轨迹。但令他困惑的是,他时不时就会发现一条规模相似、朝相反方向偏转的轨迹曲线。
起初,安德森认为这一定是由向上移动的电子形成的。但密立根提醒他,宇宙射线来自太空,而不是地面,所以形成这些轨迹的一定是从太空降落的带正电的质子。[24]安德森并不信服。作为唯一已知的带正电粒子,质子要更大一些,所以它们的轨迹应该比电子的轨迹宽,但这些轨迹并非如此。他们争论起来。安德森改进了他的实验。最后,在新证据的支持下,他大胆宣布他发现了一种新型的亚原子粒子。而且这种粒子非常古怪,除了带的是正电荷外,它和电子完全一样。
不管是卢瑟福、玻尔、薛定谔,还是奥本海默,这些著名的量子物理学权威没有一个相信他。[25]每个人都知道原子只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负电子、带正电的质子,以及刚刚发现的不带电荷的中子。正电子不可能存在。可是,就在6个月前,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宣布,他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角力数年之后,被迫做出了一个奇怪的预测。应该有与电子质量相同但电荷相反的粒子。就连狄拉克自己都怀疑自己的说法,然而安德森找到了。这种新的亚原子粒子是反电子——有史以来发现的第一种反物质粒子。当时,它被命名为正电子。
(如果你认为反物质听起来与日常生活很远,那你可能有兴趣知道,你和正电子的熟悉程度比你以为的更高。我们体内有少量的天然放射性钾以分子形式存在,它们具有发送神经信号的功能。每天大约有0.001%的钾原子衰变,释放正电子。如果你体重为150磅[26],你每天会产生近4000个正电子。[27]但它们不会逗留太久。每个正电子都会迅速遇见一个电子,在相互摧毁时,它们会留下一次小小的辐射爆发以证明自己。)
就在安德森无意间发现正电子的两年后,他又捕获了另一种粒子——μ子。[28]令人费解的是,它的电荷与电子相同,却比电子重200多倍。听到这个消息时,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问:“那是谁定的?”[29]
赫斯、威尔逊和安德森都因自己的发现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物理学家发现了一些人们曾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新型亚原子粒子。事实突然变得很明确,原子不仅仅包含电子、质子和中子。我们再也不能确定我们体内的原子最终由什么构成。
但是物理学家仍如盲人摸象。为了找到原子的最小成分,他们仍然需要创造性的新工具。幸运的是,又一项至关重要的发现很快就会出现,这要归功于玛丽埃塔·布劳。她是一位五英尺高、性格内向的奥地利研究员,而她的贡献将被长久遗忘。和威尔逊一样,她开创了一种方法,可以“看见”显微镜无法显示的微小物体。
20世纪第二个十年,布劳就读于女子公学预备学校,由此对物理产生了兴趣。她的兴趣在维也纳大学变得更加浓厚,她在那里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当时有不少欧洲女性受玛丽·居里的启发,研究令人费解的放射性新现象,布劳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前,居里夫人及其丈夫皮埃尔发现了一种近乎神奇的新元素——镭,它的放射性比铀强一百万倍。它似乎能提供“取之不竭的光和热”,令科学家兴奋不已。在随后的镭热潮中,你可以买到加镭的肥皂、雪茄、牙膏和糕点,甚至还有加镭的家具清洁剂和肛门栓剂。[30](居里夫人没有意识到危险,自己也因暴露于辐射照射而英年早逝。[31])镭是从铀矿石中提取的,欧洲唯一的铀矿属于奥匈帝国。因此,顺理成章,维也纳建立了一个镭研究所,布劳作为有才华的实验者也在那里找到了工作。
1925年,她的导师,一位物理学家,给了她一项艰巨的挑战。她能不能用照相底板来探测两个原子核相撞时喷射出的质子的路径?[32]实际操作甚至比听起来还要难得多。她要尝试找到比原子更小的单个粒子的轨迹。她百折不挠,系统地尝试使用浓度更大的感光乳剂,测试了底板显影的新技术,并竭力解释那些几乎无法察觉的印痕。多年后,她竟然成功了,她不仅捕捉到了微乎其微的粒子的路径,还利用其来测量粒子的能量。这显著证明了她技术的前景。
然而,布劳这些年在研究所工作时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她养活自己靠的是做家教、在医疗公司兼职,以及家人的帮助。当她开始获得国际认可时,她鼓足勇气申请薪水。但别人告诉她,这不可能——她是犹太人,而且是女人。[33]
20世纪30年代初,布劳改进了她的方法,并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雄心勃勃的目标:探测宇宙射线中的粒子。然而,她面临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布劳总是渴望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因此,在遇到赫塔·万巴赫尔——一位郁闷地学习法律的年轻女性时,她慷慨地提供了帮助。[34]万巴赫尔成为她的学生、助手,并最终成为她的下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劳的慷慨反而给自己带来了困扰。1933年,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在奥地利夺取政权。将犹太人逐出学术圈的呼声不绝于耳。而布劳的这位门徒成了非法竞争对手纳粹党的早期成员。[35]更糟的是,万巴赫尔与一个更狂热的纳粹分子发展了婚外情,对方是已婚物理学家,名叫格奥尔格·施泰特尔,后来成为该研究所的所长。[36]布劳和万巴赫尔还在一起工作,但两人曾经温暖友好的合作变得紧张起来。
1937年,布劳最终准备好尝试探测宇宙射线。她的照相底板可能比巨大的云室更有优势,它们也更易于运输至宇宙射线最强的高海拔地区。而且她可以把它们长时间留在那里,这大大增加了她捕获稀有粒子的机会。布劳和万巴赫尔只需乘坐悬挂式缆车,便抵达了维克托·赫斯建在哈弗莱卡峰7500英尺高的峰顶的研究站。她们满怀期待地放置特制的照相底板,使其朝向天空。
4个月后,她们回来收回底板。回到实验室后,她们通过显微镜仔细观察,而后欢欣鼓舞。底板上蚀刻着细长的线条,她们捕捉到了不可见粒子从太空疾驰而下的轨迹。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许多线条源于同一个点。一束宇宙射线击中感光乳剂中的一个原子核,使之分裂,喷射出多达12个更小的粒子,形成了星形图像。[37]布劳的发现引起了世界各地物理学家的兴趣。她多年的实验获得了成果。她开创了一项新技术,它有助于揭示我们体内最小的粒子。
不幸的是,她几乎没有机会使用这项技术。1937年,随着奥地利反犹主义的抬头,施泰特尔逼迫布劳把她的工作交给她的下级合作者,并要她离开研究所。万巴赫尔对待布劳时而无礼,时而大方。极度痛苦的布劳考虑放弃自己的研究。但接着,她意外得到了一个暂时的喘息机会。她以前的朋友兼同事埃伦·格莱迪奇得知了她的困境,邀请她到奥斯陆大学(当时的名称为皇家弗雷德里克大学)待几个月。1938年3月12日,布劳带着她最新型的底板,乘火车离开了。[38]她从火车窗口看到德国军队正迅速越过边境。那是德奥合并,是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日子。第二天,希特勒亲自进入维也纳,令他的崇拜者欣喜若狂。
挪威提供的只是一个短期避难所,但幸运的是,爱因斯坦听闻了布劳的困境。在他的帮助下,8个月后,她在墨西哥城找到了一份教学工作。她担心战争一触即发,便搭乘最早的班机离开了奥斯陆。遗憾的是,它属于一家德国航空公司。当飞机降落在中转城市汉堡时,布劳被传唤。纳粹官员似乎很清楚他们要找什么。他们翻遍了她的行李,抢走了她的照相底板,才让她离开。[39]
在维也纳,万巴赫尔在布劳留下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并开始因两人的共同研究成果而获得荣誉。布劳伤心欲绝。尽管她后来在美国获得了一系列学术任命,她却再也无法恢复重新研究宇宙射线的动力。60多岁的时候,她需要进行费用高昂的白内障手术,但在美国负担不起手术费,不得不回到维也纳。她在镭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被冷待,并且依然没有薪水。另外,她愤怒地发现,施泰特尔尽管与纳粹有明显的联系,却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允许回到一所名牌大学就职。[40]布劳于1970年去世,她的成就在她的祖国奥地利未被认可。
与此同时,许多其他人采用了布劳开创的技术,并获得了回报。1947年,塞西尔·鲍威尔和朱塞佩·奥基亚利尼在法国比利牛斯山的一处山巅放置了灵敏的照相底板,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亚原子粒子——π介子,这是自安德森发现μ子以来发现的第一种新粒子。与μ子和正电子一样,介子也是奇异的玩意儿。它们大约比电子重270倍,可以带正电,也可以带负电,或者不带。
鲍威尔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布劳却没有被提及。她至少三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其中两次的推荐者都是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埃尔温·薛定谔,但这一切徒劳无功。
在威尔逊的云室和布劳的照相底板上,那美丽的纤弱轨迹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它们揭示了比原子更小的新粒子的存在,但几乎没有阐明图景。虽然有了正电子、μ子和π介子这样的粒子,但靠物理找到我们体内基本要素的日子倒似乎更加遥遥无期了。科学家就好像在一个井底寻找解决办法,却发现井底的深度超乎他们的想象。他们只能不断放下水桶,并满怀期望。然而,原子内部的图景甚至将很快变得更加模糊。
到20世纪40年代,物理学家知道,宇宙射线主要由原子核,以及游离的质子和电子组成。它们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冲向地球,大部分被大气层吸收。但一些高速碰撞会分裂原子,产生更小、更奇异的亚原子粒子,比如π介子和μ子,它们也会像雨点一样落到地球上。
因此,研究人员当下决定尝试一种更直接的方法。与其等待宇宙射线偶尔大发慈悲,发射一个新粒子,为什么不操纵粒子撞在一起,看看是否有新的粒子会像高速公路车祸飞出的碎片般喷射出来呢?粒子搜寻者开始建造原子对撞机,他们更喜欢称之为粒子加速器,使电子与电子、中子与中子以惊人的速度相互撞击。
1949年,8所美国大学在纽约的布鲁克海文联合建造了第一台庞大的原子对撞机,并给它起了一个乐观的未来主义名字——宇宙加速器。它的内部结构看起来像是一架刚被空运来做调试的飞碟。物理学家将粒子发射进一圈200英尺长的环形轨道,轨道由288个6吨重的磁铁环绕。这些装置控制着粒子绕轨道运行,每隔10英尺设置的微波发射管会提升粒子每一圈绕行的速度,就像在加速的旋转木马上推动它们一样。研究人员在一堵两英尺厚的混凝土墙后面操作了这个30亿伏的设备。等终于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后,他们便可以在4/5秒内将粒子发射130000英里,使它们加速到接近光速。[41]
这些撞击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研究人员欣喜地发现了更小粒子的轨迹。撞击点周围布置了布劳的照相底板,还有气泡室——威尔逊云室的类似物。它们的灵敏度高得惊人,可以探测到直径小于一百万亿分之一英寸、存在时间小于十亿分之一秒的粒子。[42]突然之间,最基本粒子似乎触手可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随着新发现数量的攀升,喜悦变成了困惑和惊愕。[43]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物理学家面对数十个奇异粒子组成的“动物园”,大惑不解,一头雾水。K介子、λ粒子、Σ粒子、Ξ粒子、超子,名单不断加长。“如果我能记住所有这些粒子的名称,”费米抱怨道,“我就不是物理学家,而是植物学家了。”[44]粒子物理学家注定要成为头衔好听的编目员吗?他们看到了一些表明这些粒子拥有共性的迹象,但没能找到统一的体系将它们联系起来。科学家想在宇宙混乱的表象下发现一种简明的秩序,但这一梦想到此为止了。此时,对最基本粒子的探索似乎裹足不前。
局面一直混乱不堪,直至1961年默里·盖尔曼加入。
盖尔曼是个神童。他3岁时就能心算大数相乘,15岁进入耶鲁大学。[45]他是那种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他老是写不完论文,经常逃课,却总是在考试中名列前茅。32岁时,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在芝加哥大学与传奇人物费米共事,并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他会说13种语言,包括高级玛雅语。他的合作者谢尔登·格拉肖回忆:“不用认识多久,他那咄咄逼人的博学就会让你明白,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知识都远超你,不论是考古学、鸟类、仙人掌,还是约鲁巴神话和发酵学。”[46]照片上的盖尔曼通常眼神温暖,笑意藏在厚重的黑框眼镜后,但他易怒且傲慢。他喜欢贬低与他意见不同的人,包括圈子里的另一个天才——理查德·费曼,这位合作者后来变成了他的竞争对手。
盖尔曼选择研究粒子物理学,他有一种不寻常的天赋,善于辨识潜在模式。经过多年研究,他发现他可以运用一种晦涩的代数理论形式,根据粒子“动物园”里所有成员的性质——电荷、质量、自旋和“奇异数”(这种性质似乎可以预测一些粒子衰变为更简单粒子所需时间的差异)——将它们分组,于是他迎来了顿悟时刻。在一次令人惊叹的关于自然界如何映射数学的演示中,他发现这些粒子可被分成8个几何形状组成的不同集合,叫作八重态。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八重法”,幽默地向禅宗致敬[47](毕竟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加州[48])。也许它终将使粒子物理学家得到启迪,结束他们的痛苦。[49]盖尔曼的八重态将粒子分组,这些分组与粒子性质一致的程度,就如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将元素排序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几何图案中有缺失粒子的地方,盖尔曼预测人们将发现新的粒子。
但盖尔曼对发表他的理论感到忧虑,以至于两次从《物理评论》撤回了论文。[50]最后,他提交了一篇关于粒子性质的论文,并谨慎地把关于八重法的突破性意见藏在文章末尾。
正如科学界常见的那样,另一个人同时得出了同样的理论。这又是一名神童,他名为尤瓦尔·内埃曼,当时是物理学家,后来成为以色列内阁成员。两人分享了发现这一晦涩理论的荣誉,它起初看似完全不可能奏效。[51]他们的理论认为,应该还存在人们未曾于自然界中见过的粒子,所以我们不清楚两人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但数年后,布鲁克海文的一项实验使盖尔曼大受追捧。他曾预测了一种特殊粒子的性质,它在他的一个几何集合中是缺失的,被他称为Ω-。实验人员开始寻找它。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加速器上安装好必要的设备。而后他们开始每天拍摄数千张照片,照片如此之多,他们不得不雇用了长岛的家庭主妇日夜轮班来帮助分析它们。[52]在拍了9万张照片之后,他们一无所获。但到了第97025张,他们发现了匹配的现象。[53]盖尔曼早已预见了Ω粒子的性质。八重法被证实了。
盖尔曼得意于他的理论,但并不满足。实验者编目的粒子数量多得荒谬,但他没有减少这一数量。他也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与八重法体系契合,但一定有某种潜在模式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已知粒子肯定是由某种更简单、更基本的东西构成的。
1963年3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拜访物理学家罗伯特·瑟伯尔时取得了突破。瑟伯尔一直在琢磨八重法的运算,他怀疑其底层代数可能揭示了一种以三为基础的深层模式。在教工俱乐部吃午饭时,他问盖尔曼,八重态中的每个粒子是否可能由三个更小的粒子组成。
“这将是个有意思的怪论。”[54]盖尔曼说。
“馊主意。”一起吃饭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反驳道。盖尔曼拿起一张餐巾纸,开始潦草地写下这个建议为什么古怪。问题在于,如果每个粒子都由三个更小的粒子组成,那么每个更小的粒子就必须带有1/3或2/3个正电荷或负电荷。没有人见过分数电荷。那它们怎么可能存在呢?这似乎不太可能。
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盖尔曼,第二天,他发现自己又在思考它。他开始想知道,是否有一种奇怪的方式使分数电荷得以实际存在。假设带分数电荷的粒子被禁锢在一个带完整电荷的较大粒子中,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无法探测到它们。它们永远无法摆脱困住它们的大粒子。这似乎很不可信,甚至古怪得不可能成真。但他又想,管他呢,为什么不呢?[55]为了梳理这个念头,他随意地把这些奇异粒子命名为“quack”或“quork”,并最终选择了“quark”(夸克),这个荒唐的名字源于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quark”在德语中有“胡言乱语”的意思,盖尔曼得知这一点时也被逗笑了。)
盖尔曼认为他提出了一个聪明的理论,但也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于是他想知道,他的带分数电荷的粒子是否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数学虚构概念。[56]他担心论文可能被拒,便决定不把它交给《物理评论快报》的谨慎的编辑。他把它寄给了《物理快报》,那里的编辑更乐于发表“疯狂”的想法。[57]
再一次,有人进行了相似的头脑风暴。这一次,盖尔曼的同事、过去的学生乔治·茨威格独立地提出了分数电荷粒子的概念[不过他称它们为埃斯(ace),而非夸克,并推测它们可能有四个,而不是三个]。但茨威格是一位更年轻的科学家,当时他在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工作,那里有世界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而该机构对论文发表的地点和形式有限制。茨威格对部门主管给他设置的障碍感到非常挫败,以至于放弃发表论文。[58]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他只是给人们传阅了两份本来准备发表的草稿。他回忆,人们对他的论文“基本上不太温和”。一位上级科学家给他贴上了骗子的标签,并阻挠他在伯克利担任教职。[59]茨威格最终心情苦涩地离开了物理学界,转投神经生物学界。
和埃斯一样,夸克一开始也被排除在外。粒子中的分数电荷从未被探测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被探测到,这一理论似乎过于牵强。情况在1968年夏天发生了变化,盖尔曼的竞争对手理查德·费曼用量子物理学告诉人们,斯坦福大学的加速器实验证明了这些电荷的存在。在他的演示中,电子从质子上反弹回来,其表现就好像质子里有三个坚硬的实体。凭借云室、布劳的照相底板、粒子加速器,以及盖尔曼的直觉与数学层面的敏锐,科学家终于探测到了夸克——尺寸是沙粒的一百万分之一。[60]《纽约时报》写道,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开始打开通往物质最内部秘境的大门”[61]。
在过去的50年里,怀疑已经转变为深信。人们普遍认可夸克是粒子“动物园”中所有成员的终极基本要素,包括你身体原子中的所有质子和中子。夸克有6种类型,它们强相互作用的媒介是被盖尔曼称为胶子的交换粒子,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们把粒子黏合在一起。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夸克有分数电荷。但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力,它阻止带分数电荷的夸克逃离质子和中子。夸克越往外移,束缚它们的力会越强,就像被拉伸的橡皮筋一样。科学家估计,夸克所承受的压力超过宇宙中任何已知的压力,比海底最深处的压力大一千亿亿亿倍。[62]盖尔曼的理论得到了其他人的扩展,如今已处于不容挑战的地位。这一重大突破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
虽然你可以说盖尔曼发现了构成我们乃至世间万物的最基本粒子,但公平地说,你还包含了多得多的其他东西——真空。你可能认为你是固体,但那是一种幻觉——你的原子中有99.9999999999999%的部分都是空的。原子中的真空之海是如此之大,如果你把一个氢原子的原子核放大到网球那么大,它的电子将在大约一英里外旋转。如果你把你的电子、质子和中子之间的空间全部去掉,你将变得不比一粒大灰尘更大。你可以把全人类塞进一块方糖里。[63]
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身体如此空荡,为什么我们却感觉如此坚实?答案是,当我们碰触桌子这样的东西时,原子实际上并不相触。相反,你手指的电子和桌子的电子会相互排斥。所以你的原子并没有实际碰触桌子,它们在桌子上方波动,诱使你的神经产生触觉。物理学家会告诉你还有其他事情在发生。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相同的粒子不能占据相同的空间。因此,当原子相互靠近时,它们的电子会被迫以不同的模式围绕原子核高速旋转,这种旋转产生了排斥能,使它们无法实际接触。
迄今为止,科学史上的所有观察结果都告诉我们,除了真空,你和所有已知物质都只由三种基本粒子组成:电子、夸克和胶子。胶子是无质量的交换粒子,它们将夸克黏合成质子和中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一个集合,包含了大约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万亿亿亿)个电子、数十倍于前者的夸克和无数个将夸克黏合成粒子的胶子。
盖尔曼的发现使我们能将基本粒子的历史追溯至它们被召唤出来的那一刻。那是138亿年前,没有宇宙,没有空间和时间。而后,就在大爆炸那一瞬间,夸克、胶子和电子从一个密度无穷大的小点中喷射出来。于是砰!我们的旅程开始了。创造我们的粒子在超高温等离子体中旋转、跳跃、聚集。不到1毫秒后,胶子开始把夸克黏合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3分钟内(根据爱因斯坦的方程和对宇宙中物质总量的估计),等离子体稍微冷却。这使得胶子携带的强大核力得以发挥作用。它们开始将质子和中子黏合在一起,创造出我们这个宇宙中最初的原子核。
其中3/4是最简单的元素——氢,它的原子核中只有1个质子。这意味着你体内所有4亿亿亿个氢核,都在大爆炸3分钟后就形成了,它们约占你质量的10%。
第二简单的元素氦(有2个质子和2个中子),以及极少量的锂和铍(分别有3及4个质子和中子),也在旋转的原初等离子体中孕育出来。但目前仅此而已。
在大约2亿年的时间里,宇宙极度乏味。那才是真正的黑暗时代。没有什么可看的,也没有光让它可以被看到。在宇宙膨胀的过程中,只有4种闲置元素组成的云团飘浮在黑暗空间里。
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这4种最早出现的元素不可能凭自己创造出生命。毕竟,你的身体含有60多种其他元素,从铁和硒,到氟和钼。而你是存在的,这怎么可能发生?你体内的其他原子是如何产生的?让它们得以存在的是什么庞大的能源——等同于一千亿亿亿枚氢弹?[64]
第一条意想不到的线索将来自“哈佛第一人”,她碰巧是一名意志坚定的英国女性。
注释
[1]Rhodes,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30—31.
[2]Blackmore,Ernst Mach,321.
[3]英寸是英美等国使用的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2.54厘米,12英寸为1英尺。——译者注。
[4]量子物理学家很快就会发现,电子的轨道并没有这样容易预测。现在,他们把电子的轨道路径视为最可能找到电子的电子云。
[5]Close,Particle Physic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14.
[6]De Angelis,“Atmospheric Ionization and Cosmic Rays,” 3.
[7]Gbur,“Paris:City of Lights and Cosmic Rays.”
[8]Bertolotti,Celestial Messengers:Cosmic Rays:The Story of a Scientific Adventure,36.
[9]Kraus,“A Strange Radiation from Above,” 20.
[10]赫斯的部分叙述被翻译成英文,并刊载于:Steinmaurer,“Erinnerungen an V.F.Hess,Den Entdecker der Kosmischen Strahlung,und an Die ersten Jahre des Betriebes des Hafelekar-Labors”。
[11]“The Zenith Tragedy”;and Oliveira,“Martyrs Made in the Sky.”
[12]1英里=1.609344公里。——编者注。
[13]Ziegler,“Technology and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950.
[14]Walter,“From the Discovery of Radioactivity to the First Accelerator Experiments,” 28.
[15]De Maria,Ianniello,and Russo,“The Discovery of Cosmic Rays,” 178.
[16]引自:Nobel Lectures Physics:Including Presentation Speeches and Laureates'Biograp-hies,1922—1941,215。
[17]Pais,Inward Bound:Of Matter and Forces in the Physical World,38.
[18]两年后,J.J.汤姆孙发现阴极射线管内的阴极“射线”实际上是电子流。
[19]Pais,Inward Bound,39.
[20]Crowther,Scientific Types,38.
[21]BBC对威尔逊的采访,载于BBC纪录片《云室中的威尔逊》的文字记录。
[22]Nobel Lectures Physics,216.
[23]Anderson,The Discovery,25—26.
[24]Anderson,The Discovery,29—30.
[25]Hanson,“Discovering the Positron(I),” 199.
[26]磅是英美等国使用的重量单位,1磅=0.4536千克。——译者注。
[27]Sundermier,“The Particle Physics of You.”
[28]今天我们知道,撞击地表的宇宙射线粒子大都是μ子。每秒约有10个μ子穿过你的身体。宇宙射线每年给你增加约27毫雷姆的辐射剂量,几乎相当于3次胸部X光。[松德迈尔,《你的粒子物理学》(The Particle Physics of You)]
[29]Close,Marten,and Sutton,The Particle Odyssey: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Matter,69.
[30]Rentetzi,Trafficking Materials and Gendered Experimental Practices,2;and Miklós,“Seriously Scary Radioactive Products from the 20th Century.”
[31]即使到了今天,她的文件也具有很强的放射性,研究者在检查它们前必须穿上防护服。
[32]Sime,“Marietta Blau:Pioneer of Photographic Nuclear Emulsions and Particle Physics,” 7.
[33]伦特兹,美国物理研究所对利奥波德·哈尔佩恩的口述历史采访。
[34]伦特兹,美国物理研究所对利奥波德·哈尔佩恩的口述历史采访。
[35]Galison,“Marietta Blau:Between Nazis and Nuclei,” 44.
[36]Sime,“Marietta Blau,” 14.
[37]Rosner and Strohmaier,Marietta Blau,Stars of Disintegration,159.
[38]Rentetzi,“Blau,Marietta,” 301.
[39]伦特兹,美国物理研究所对利奥波德·哈尔佩恩的口述历史采访。
[40]伦特兹,美国物理研究所对利奥波德·哈尔佩恩的口述历史采访。
[41]Plumb,“Brookhaven Cosmotron Achieves the Miracle of Changing Energy Back into Matter.”
[42]Close,Marten,and Sutton,The Particle Odyssey,13.
[43]Riordan,The Hunting of the Quark:A True Story of Modern Physics,69.
[44]引自:Riordan,The Hunting,69。
[45]Johnson,Strange Beauty:Murray Gell-Mann and the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Physics,35.
[46]Glashow,“Book Review of Strange Beauty:Murray Gell-Mann and the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Physics,”582.
[47]佛教教义中有“八正道”,意为八种方法,包括正见、正念、正定等。——译者注。
[48]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是反主流文化的时代,年轻人反叛社会,宣扬佛教禅宗,加州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译者注。
[49]Bernstein,A Palette of Particles,95.
[50]Johnson,Strange Beauty,194.
[51]Johnson,Strange Beauty,208.
[52]Crease and Mann,The Second Creation:Makers of the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Physics,275.
[53]Johnson,Strange Beauty,217.
[54]Riordan,The Hunting,101.
[55]Crease and Mann,The Second Creation,281.
[56]Johnson,Strange Beauty,283—84.
[57]Crease and Mann,The Second Creation,284.
[58]Charitos,“Interview with George Zweig.”
[59]Zweig,“Origin of the Quark Model,” 36.
[60]Butterworth,“How Big Is a Quark?”
[61]Sullivan,“Subatomic Tests Suggest a New Layer of Matter.”
[62]Chu,“Physicists Calculate Proton's Pressure Distribution for First Time.”
[63]Sundermier,“The Particle Physics of You.”
[64]Cottrell,Matter: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