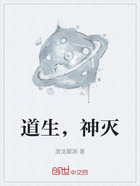
第22章 仙
离火脉主心,启脉时心火透体化作三足金乌,翼展焚尽脏腑淤塞,古籍载“金乌过处,沉疴尽焚“。
“医者医世当先医己,如何医?”李仙声如春风,凉而不寒,去何秦身上那股燥意。
“不医即自医。”何秦将所学道出“身体自成天地,效法阴阳五行。当如同星辰般,日出而行,月出则止轮转往复。如此身体自然不会生疾,故不需自医。如今或阴阳颠倒,五行运转过快或过慢,以至于内部开始崩塌,故而五脏六腑俱损。或外邪入侵而身体无法运转生病。”
“不医方为医。”何秦有条不紊讲起,“人身自蕴周天,阴阳化生五行轮转。本应如星宿循轨,昼升夜伏,吐纳有度——”他指尖在虚空画出北斗轨迹,“本无病邪可侵,何须药石相加?”
话音忽转沉郁:“而今病者阴阳倒悬,或五行疾驰如奔马,或滞涩似冻川。脏腑相冲如乱弦,经脉淤塞若断江。兼风邪趁虚而入,脏腑气机尽乱,安得不损?”
李仙指节扣响青玉案,金石声里透出寒意:“医道至简,不过调燮阴阳尔。五气顺逆如四时流转,自能消病于未形。”
“却有人治足溃先斩其足,待腿腐再断其腿——刀光追着腐肉跑,可曾抬眼看过患者眉间死气?这等断水止沸的治法,与屠夫何异?”
李仙自然是大骂:“不知五脏六腑,四肢皆是相通的,内部受损,只知割肉,庸医。”
药方若能一次将病去之,而后还有谁来看医呢?世间庸医比比皆是,治死耗死的冤魂比比皆是。
市面上那些所谓的“千金方”,把桂阳单拆作十三味汤,非金丝楠木匣不锁“残方”,非琉璃瓶里不装“三更露”。更将八两陈皮炒成天价龙鳞,使典尽薄田易不来半剂真方,卖尽骨血求不得一味正药。更可恨把青龙汤拆作十二道“秘方”,将火灵草炼成“金丝丹”。先毁千年验方,再哄抬新药价码,硬生生把悬壶济世变成秤上生意。
所谓“良医”,早把望闻问切炼成了秤金戥银的手艺。
真正的药方自是简单无比,那些所谓的千年医药世家不过是将古代医圣流传下的古方拆开化为数个药方,而真正的单方则将其作为传家密宝。再联合其他医药世家对市面上流传的廉价古方定为邪术,大规模毁去廉价古方,推行昂贵新药者比比皆是。殊不知这些所谓的新药也不过是从这些古方得来。考愚弄患者,将这些能治好一部分但无法断根之物的残缺之药用于治人,获得金银可笑、可悲至极。若古之医圣活了过来,非得将这些蛀虫全都灭了不可。
这世间大部分病者耗尽家产,卖儿卖女皆不能活,取得那无用之药,如何能愈。或吊着一口气,能愈又不可愈;或割肉,以至残缺阴阳不合,五行不转,最后活活病死。
……
相传三百年前,李家先祖李青囊凭一手金针度厄之术行走江湖。白麻衣角总沾着药香,青驴背上载满晒干的艾草,逢村便悬壶问诊,遇疾必施药相救。最奇的是他竹篓里常年备着三枚铜钱——病愈者若强塞诊金,他便将铜钱抛入病家水井,笑称“买一瓢清净水,足矣”。
后来李家先祖于山中采药,遇遇一仙人赠予上卷《太玄素经》。
恰好那年灵州发瘟,李青囊背着药篓走遍三十六郡治瘟疫,不收半枚钱。
那年腊月飞雪夜,有位白衣老者踏雪而来,袖中飞出下半卷《太玄素经》没入李青囊的药箱。“悬壶济苍生,自有天垂怜”,晨雾里传来飘渺话音,“后世若有承志者,可踏仙路”。从此李家祠堂便供着那卷泛黄经书,檐下悬着三枚生锈的铜钱。
待到李仙十六岁这年,青囊堂的匾额已落满尘灰。父亲李凌云攥着祖训在祠堂独坐到天明,月光爬上“但求心安”四个褪金大字时,终于把女儿唤到跟前。
青瓦檐角坠着露水,李仙正擦拭药柜里那尊传了七代的青铜药炉。炉身铭文斑驳处依稀可辨“太素“二字,正是当年仙人授经时留下的信物。
“上月爹冒雨去收祖训木匣。”李仙推开北窗,远处山道上新坟的招魂幡隐约可见,“他说若这代绝了嗣,就把《太玄素经》埋进太素炉,连同...”话音忽止。何秦看见木匣边缘焦痕,想起元宵那夜李凌云醉后举着蜡烛逼近祖训的模样。
“今日该去三十里铺看诊了。”李仙将祖训木牌重新挂上门楣,熹微晨光里,“不求钱财,但求心安”八个字在晨光中熠熠生辉。
她祖先自次定下以解救天下病者为本的祖训,只是好医往往混不下去。到了李仙她这一代就只剩下她这个独苗了,但何秦和她有缘倒是做了个帮手。
她先祖便传下游医这一祖训,李家后辈需去游医,不收钱财,只为医人。
这游医也不知需多少日,像他父亲李凌云已经有两月未归。
李仙已是十七,本来她这一女子不该接触医术的,人心险恶,男子且难以控制,何况一弱女子呢?但她父亲再不传她医术,怕是要断在他这一代了,李仙自然是传承下去。
李家本应十六岁就独自去行医,但他父亲自是不放心,带着她去,后面就捡了个何秦了。
这故事但太过久远,无人知真假。李家一直恪守祖训,但不言成仙,到了李凌云这一辈都要绝后了。李凌云都想把这祖训给烧了,从此就不会有这破事,也可以昧着良心去挣钱。
“不求钱财,但求心安。求财者勿入此门。”
何秦也是感到无奈,也难怪这一脉人丁稀少。李仙他爹当年都没钱娶妻,但她娘见他当真是个悬壶济世的良医,自是不要分文嫁给他。当时她娘家为此和她娘断了关系,这李仙倒是和她娘一样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