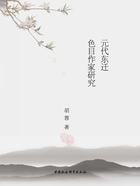
第二节 色目人的西域文学渊源
回望蒙元时代,当我们立足中亚,不仅能看到滔滔黄河与江淮烟雨,还能看到额尔齐斯河与贝加尔湖;不仅能看到华北平原与江南丘陵,还能看到帕米尔高原与钦察草原;不仅能看到奎章阁与玉山雅集,还能看到《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辞典》;不仅能听到黄钟大吕与咿呀南曲,还能听到嘹亮的畏兀儿牧歌和阿拉伯商队的驼铃。蒙元帝国神奇的魅力恰在于此。元代色目家族从西域来到中原,背负西域文学传统开始了汉语言文学的创作,色目家族的文学活动从学写第一个汉字,学说第一句汉话开始,他们的汉文诗歌创作以弱而入,以盛而终,色目作家从无到有,由星星之火渐成为燎原之势,成为元代诗坛的劲旅,推动了元代诗歌的发展。
色目家族不是孤立的,色目家族的周围存在着一个与家族情趣协调一致的社会文化圈,被包含在一个更广大的文化体系之内,而西域文学传统则是这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性格与地理环境相关联。千百年来,西北各民族游走于从漠北草原到天山至中亚的广阔土地上,妩媚的格桑花盛开在万里草原上,连绵起伏的小山包勾勒出草原温柔的曲线,牧人策马奔驰,驱赶着成群的牛羊,河水缓缓流淌,马儿在湖边静静吃草,远方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挺拔。这里还有黄沙漫天,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千里无人。酷烈的太阳,凛冽的寒风会使人两颊红而粗糙,一场持续的暴风雪会使牛羊成批冻死,他们需要到几千里外重新安置家园,一次迁徙要走几千里。《世界征服者史》生动描述了游牧民族的一次迁徙,“畏兀儿各部和各族,每逢传来马嘶声、犬吠声、牛鸣声、骆驼吼叫声、野兽咆哮声、羊群咩咩声、鸟雀嘁喳声、婴儿呜咽声,都从中听见一种‘喝起、喝起!’(kǒch、kǒch)的呼喊,因此,他们便从他们驻扎之地挪动。不管他们停留在何地,都听到‘喝起,喝起!’的呼喊。最后,他们来到后来兴建别失八里的平原,那呼喊才平息下来。”[50]他们对于空间的概念与中原农耕民族不同,中原的农民世世代代定居在一个村子里,大部分人一辈子就行走在方圆几里之内。从漠北高原行程万里到中亚消灭对手、奔袭数千里到云南作战,建立一个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在游牧民族看来也许真的不算什么。这种宏大的气魄胆识是游牧民族的民族性格在军事上的体现,粗犷豪迈、狡黠沉着的民族性格与他们的地理环境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这是以定居为主的农耕文化难以养成的。
古代突厥文碑铭如《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是用韵文写成的,是突厥语族的第一批文学作品。
前面我曾征战到山东平原,
几乎到达海;
右面我征战到焉耆,
几乎到达吐蕃。(《阙特勤碑》南面第3行)
我父可汗的军队像狼一样,
敌人像羊一样。(《阙特勤碑》东面第12行)
我的眼睛好像看不见,
我的智慧好像迟钝了。(《阙特勤碑》北面第10行)[51]
西北各少数民族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强,有着良好的语言修养。11世纪喀喇汗王朝时期经典之作《福乐智慧》具备了高超的语言技巧,代表了古代维吾尔、突厥语文学创作的成就。
Qaz ördäk quɤu qïl qalïqïɤtudï,
qaqïlayu kaynar yoqaru qodï.
qayusï qopar kör qayusï qonar,
qayusï capar kör qayu suw  .
.
kökiš turna köktä ünün yangqular,
tizilmiš titir täg učar yilkürär.
ular quš ünin tüzdi ündär  ,
,
silig qïz oqÏr täg köngül birmišin.
ünin ötti käklik külär qatɤura,
qïlzïl aɤzï qan täg qaši qap qara.[52]
译文:
鹅、野鸭、天鹅和克勒鸟布满天空,
它们上下飞翔啼鸣。
你看,一些飞起又落下,
你看,一些在游泳,一些在喝水。
灰色大雁的叫声在空中回响,
像长长的驼队在飞翔。
山鸡鸣叫,呼唤其伴侣,
好位年青姑娘召唤心爱的人。
鹧鸪在高声笑,
红嘴如血眉如漆。[53]
诗歌运用比喻、拟人手法描绘了美好的自然环境,鹅、鸭在水中游泳,天鹅、克勒鸟在天空自由翱翔,大雁、鹧鸪的鸣叫声回旋在天空。优美的大自然激发了姑娘对爱情的渴望,诗作刻画了姑娘的内心活动,歌颂了爱情的美好。诗作还运用对话来叙事写景:
大地充满香气,樟脑(指雪)消失,
世界要打扮得漂亮。
枯树穿上了绿装,
打扮得五彩缤纷。
大地用绿的丝锦遮盖了地面,
契丹商队运来了中国货。
(大地说:)千百年来我孤单无倚,
我脱掉了丧服而穿上白貂皮。[54]
西北各民族骁勇善战,他们还擅长描写战斗者的磅礴气势和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
雷鸣如擂击战鼓、
闪电如挥舞可汗利剑。
一个剑出鞘要征服世界,
另一个誉满四方。[55]
外来宗教的不断传入,不但对原始宗教产生影响,而且对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呈现一种宗教与文学杂糅交融的格局,产生了带有各种宗教烙印的文学作品。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突厥语民族受到阿拉伯、波斯文学的影响。古代维吾尔诗歌每行诗音节相同,七个或八个音节,是三四或四四节奏,押头韵和脚韵,四行一段,这种形式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现代的民间诗歌中依然保留着。10世纪后,伊斯兰教兴盛,《福乐智慧》等突厥语书面文学采用了阿拉伯的阿鲁孜格律,阿鲁孜格律逐渐取代原来的诗歌形式。“阿鲁孜是指以长短音节的组合、变换为基础的格律诗。”[56]“阿鲁孜韵律诗的原理与汉族的以平仄的组合、变换为基础的律诗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处是汉族律诗中的平仄以声调为基础,而阿鲁孜则以长短音节为基础。长短音节的区分是阿拉伯语(以及波斯语)内固有特点。在阿拉伯语今所谓长音节是指辅音后跟有长元音或以辅音结尾的音节,所谓短元音是指辅音后跟有短元音的音节。”[57]阿鲁孜韵的每行诗音节数相同,组合起来的长短音节数也相同。13、14世纪的察合台语和察合台文就是突厥语民族与波斯文化交流的结果,察合台语言文字是在古代维吾尔语的基础上,吸收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成分而形成的,在突厥语民族中通行。
总之,在元代之前,西北各民族就有了悠久的文化传统,良好的文学语言的修养,从民间歌谣、宗教文学到文人创作,西北各族不断创造着文学的奇迹,文化地层层层累积,形成了元代色目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迎接着元代色目作家的辉煌。元代色目作家是草原文化圈的骄傲,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他们的文学修养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很深的民族历史文化积淀。
[1] [法]丹纳:《艺术哲学》,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2] [法]丹纳:《艺术哲学》,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3] 李叔毅、傅瑛点校:《石田先生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4] 李叔毅、傅瑛点校:《石田先生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5] 李叔毅、傅瑛点校:《石田先生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6] 任道斌辑集点校:《赵孟頫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
[7] (元)顾瑛辑,杨镰、祁学明、张颐青整理:《草堂雅集》(中),中华书局2008年版。
[8]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9] (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
[10] (汉)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4页。
[12] 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13]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
[14]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杨志玖:《萨都剌的族别及其相关问题》,《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8页。
[15] 姚景安:《元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1页。
[16] 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7] (元)戴良:《九灵山房集》,丛书集成本。
[18] 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19] (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34、238、239页。
[20]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22]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元)危素:《乃易之金台后稿序》,《危太朴文集》卷十,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8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24] 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25] 王桐龄:《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9页。
[26] (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2页。
[27] (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95页。
[28] (元)苏天爵:《枢密句容武毅王》,《元朝名臣事略》,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7页。
[29]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大正藏》卷49,第2036号,页727c。
[30]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294页。
[31] (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70,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15页。
[32] (元)王恽:《秋涧文集》卷9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9页。
[34] (元)苏天爵编:《元文类》(上),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325页。
[35] (元)黄溍:《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文献集》卷十(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收于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0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36]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37]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38]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195《回纥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 (元)苏天爵编:《元文类》(上),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325页。
[40] (明)宋濂等:《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00页。
[41] (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43]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44] 屠寄:《蒙兀儿史记》,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732页。
[45] 陈高华:《元代内迁畏兀儿人与佛教》,《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46] (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4页。
[47] 罗贤佑:《中国历代民族史·元代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171页。
[48] 罗贤佑:《中国历代民族史·元代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49]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0]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喝起”的含义是“走”。
[51]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52]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53]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54]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页。
[55]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56]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少数民族诗歌格律》,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1页。
[57]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少数民族诗歌格律》,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