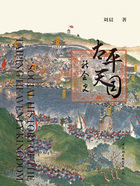
第一节 选题缘起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日趋冷落的同时,出现了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持肯定与否定的两派言论,两派倡言者言各有据,却又各持一端。否定派的代表性著作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相关部分、[6]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第2册《太平天国》、[7]潘旭澜的《太平杂说》、[8]史式的《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和《太平天国不太平》;[9]还有一批通俗性读物,如陶短房的《这个天国不太平》、月映长河的《欲望是把双刃剑:太平天国的人性透视》、梅毅的《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等。与此相对的是,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持基本肯定的言论,代表性文章有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辩证》,[10]方之光的《太平天国要对内战造成的大灾难负主要责任吗?——与凤凰网〈太平天国〉编导商榷》《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吗?——与潘旭澜教授商榷》等。[11]学界由是掀起一场关于太平天国历史评价的论战,这场论战波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秘密结社等,涉及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对以太平天国史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曾被誉为国内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的省思等重大问题。
实际上,否定太平天国的观点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有人提出。简又文在1944年出版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中提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的“大破坏”论。[12]1955年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政治》一文中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蠢的统治。……真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惨剧”。[13]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的讨论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较长时间内持续进行,持截然对立观点的两个流派也一直存在,直到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断;20世纪80年代复生,后又牵扯到“邪教”问题的讨论。其实,学术上的异见、理辨乃至争论当为学界的常态。依后生之见,抛开“非此即彼”“非正即邪”的历史窠臼,以史料和史实考辨为基础,走出全面肯定或全盘否定的学术怪圈,理性地审视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极有必要。
探讨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一个核心问题是系统把握和全面评价太平天国与民众的关系——太平天国到底代表了谁?尤其是要关注太平天国与农民的关系,因为长期以来太平天国被定性为“农民战争”“农民革命”“农民运动”。传统上,民众响应和支持太平天国被认定为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的主流。[14]要与此商榷,必须研究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的对立层面。否则便无法全面认知太平天国在瞬间烟消云散,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源。但本书并非是对太平天国的批判性研究,而是力图在梳理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客观、理性地认知民众反抗太平天国的历史现象。然而对立关系具有复杂性,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包括民众的(群体或个体)积极对立意识和行为、(群体或个体)消极对立意识和行为。所以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切入点,既能从宏观方面,也可从微观方面观察太平天国与民众对立关系的成因、表现和影响。
2010年暑期笔者随同刘平教授在浙江诸暨包村针对包立身事件的田野调查,搜集到包括4块《包村忠义祠碑》《暨阳东安包氏宗谱》《诸暨阮市包氏宗谱》在内的珍贵资料。包村抵抗是民众反抗太平天国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而民众在极度恐慌中展开的抗争行动不在少数。关于民众群体对立行为,民团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集中于士绅领导的团练;而普通农民抗粮、抗捐税的民变事件和平民领导的民团武装既是群体对立行为的重要表现,又为过去学界较少关注。经阅读资料,在太平天国治下的常熟昭文地区至少就有数十起民变事件发生,这类现象足以构成一个群体研究对象;另外,相对于团练,此类反抗行为因缺乏政治性或政治立场不甚明显而对探讨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更有说服力。因此选择以“民变”为中心,兼及比照平民领导的武装反抗事件(如“包立身”“沈掌大”等几起特殊“民团”),或可从社会经济史、日常生活史和政治史结合的视角揭示民众反抗太平天国的深层原因。以上便是“反抗反抗者”研究思路确立的大致经过。
太平天国与民众的关系是涉及太平天国社会战略和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问题。梳理民众与太平天国群体对立行为的案例,有助于总结“天国”陨落的社会层面因素和历史教训,有助于加深对太平天国在挫折中发展而又在发展中倾塌的原因的认识;同时可小中见大,管窥民众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太平天国时期及战争前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太平天国初期的基本态势是在挫折中发展。一方面,太平军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基本与清军取得战略平衡。主要原因有:太平天国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构建了极具吸引力的土地政策和营造人间“小天堂”的梦幻,大批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民众铤而走险,支援和参加太平军;清廷的内外交困、清军的极端腐朽;太平天国特有的统一的宗教、政治、军事制度激发出的战斗精神,即如洪仁玕所说:“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15]太平天国的政治宣传和动员等。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在社会控制方面受挫。1860年前太平天国建立的江西、湖北根据地极不稳固,安徽基地也局缩在安庆、庐州等军事重镇附近,天京始终没有彻底摆脱江南、江北大营的军事扼控。地方社会秩序不稳,像溃军、团练、土匪的不时破坏;在民众对立方面,咸丰三年(天历癸好三年,1853)安徽民众反对太平军政略的动乱是典型案例,甚至迫使杨秀清两次派石达开赴安庆抚民易制。[16]民众对立的原因主要有:清方的政治宣传攻势与民众的恐慌心态;太平天国地方行政无作为,导致城市像兵营,乡村一片荒芜;强制推行男女之别的社会结构调整、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和不合实际的工商政策,激起民众反感、敌对;太平天国空想的宏伟蓝图表现为现实的零实践,农民幻想破灭,原来支持、响应太平军或是持同情态度的民众逐渐失望。但是由于前期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尚能采取因时制宜的修正举措,以及军事方面的战略相持等因素(最重要的是粮食得到有效储蓄和补给),民众与太平天国的对立尚未充分展现,支持者在数量上仍占优势,太平天国的总体事态还在发展。
其次,太平天国后期的态势是在发展中倾塌。尽管后期太平天国二破江南、江北大营,开辟苏南、浙江根据地,赢得针对八旗、绿营的军事胜利,这种胜利仅是单纯的军事胜利,并未取得地方社会管理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生态的稳固。相反,乡官基层组织异化;白头军兴,民众对立;社会经济秩序紊乱(传统社会经济秩序与贡役制社会结构并行),民众反抗剧烈而出现地方社会失控,太平天国在社会下层失去政权的合法性。暂时的军事胜利无法挽救太平天国四面楚歌的败局,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愈加窘促。最后,在中外敌对势力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只能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苏、浙根据地仅维系三年左右时间,太平天国就在迅猛发展的假象中倾塌。
通过太平天国历史发展态势和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分析,也可加深对太平天国盛衰分水岭的认识。咸丰六年(天历丙辰六年,1856)天京事变的标志性意义似不足以完全说明太平天国战略全局的衰败。在军事战略方面,天京事变的确与这一时期太平天国暂时的战略退却有关。但是,事变没有造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事变后不久,太平天国迅速地再破江北、江南大营和开辟苏南、浙江疆土说明了这点——新的统一的领导核心对太平天国“中兴”发挥了作用。太平军二克江北大营,开创局部战略进攻的新局面,时在咸丰八年(天历戊午八年,1858)八月二十日,上距石达开由安庆出走之咸丰七年(天历丁巳七年,1857)八月十八日仅一年的时间。在社会战略方面,被誉为太平天国史上闪光点的洪仁玕新政、《资政新篇》和李秀成的地方建设新思维恰恰是在天京事变后诞生。而大量数据可能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指向1860年,这一年太平天国入主江南,社会战略着手执行,太平天国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承袭清制的同时,因承旧弊,并在执行方式上存在严重误差,社会失控初露端倪,埋下了太平天国亡于江南的种子。也正是在这一年,孔飞力所说的地方军事化等历史表征开始呈现——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借兵助剿”提上议程;江南团练繁兴;地方绅权反弹。[17]此外,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战略防御转入战略退却可能并非由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决定,也不太可能在某一年度内就完成转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过程,并且与大的社会背景、国际国内局势相关。过去有所忽视的是同时期某些具有密切联系的历史事件的有机结合对历史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看,直到1862年上半年太平天国仍然对东线战场的上海保持压力。太平天国的战略全局基本是在1860—1862年一段时间之内发生转变,除上述历史表现,军事方面还有:二次西征失败(1861年6月)、安庆失陷(1861年9月)、清廷借师助剿(1862年2月)、庐州失陷与陈玉成被俘(1862年5月)、天京被围(1862年5月)、上海战役失败(1862年6月)、雨花台战役失败(1862年11月)、苏南和浙江根据地被蚕食(1862年2月左宗棠入浙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