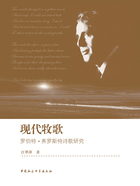
第一节 美国文学批评视野中的弗罗斯特
在美国文学史上,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弗罗斯特诗歌研究形成一股热潮,人们乐此不疲地探讨这位诗人和他的诗歌作品。继美国之后,中国学术界2000年以来也呈现出研究弗罗斯特诗歌的强劲趋势。在美国和我国,弗罗斯特及其诗歌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美国对弗罗斯特诗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早期弗罗斯特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一些诗人、文学家、批评家以及学者对弗罗斯特作出的初步的介绍和评论。
1913年4月,弗罗斯特的第一部诗集《少年的心愿》正式出版,庞德看过这本诗集后立即作出评论,该评论在1913年5月的《诗刊》(Poetry)上发表。庞德认为,弗罗斯特长久以来遭到“伟大的美国编辑们”的轻视,直到弗罗斯特逃离美国这片文化的沙漠。庞德同时指出,弗罗斯特能够较好地自然而然地讲述和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他没有虚伪和做作。在具体评论诗集中的《忽视》(“In Neglect”)一诗时,庞德认为这首诗歌是弗罗斯特个人经历的写照,讲述“他的祖父和叔叔剥夺了他对一笔数量可观的遗产的继承权,让他陷入贫困,因为他是一个无用的诗人而不是一个会挣钱的人。”[1]弗罗斯特对庞德的评论颇感不满,认为庞德误解了他的诗歌甚至是故意曲解他的诗歌,一方面是为了抨击美国编辑的大众化趋向,另一方面是以揭露弗罗斯特家庭的丑陋作为批判美国庸俗化现实的一个例证。随后在1914年12月的《诗刊》上,庞德以《现代农事诗》(“Modern Georgics”)为题评论了弗罗斯特的第二部诗集《波士顿以北》。庞德认为弗罗斯特拿着一面镜子映照自然,是一位“有意识地并准确地将自己熟悉的新英格兰农村生活写入诗中的诚实作家”。[2]庞德的这两篇评论都在美国发表,虽未对美国读者产生什么影响,却引起了英国读者及评论家的注意,成为批评界向世人推介弗罗斯特诗歌所作出的最初的权威评论。从此,默默无闻的弗罗斯特开始在现代诗坛崭露头角。1919年,弗罗斯特一个忠实的朋友、美国诗人路易斯·昂特梅耶(Louis Untermeyer)在他的专著《美国诗歌的新纪元》(New Era in American Poetry,1919)第一章的首要位置对弗罗斯特进行评价,赞扬其诗集《波士顿以北》中的戏剧性对话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新颖、最具感染力的对话,认为与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弗罗斯特找到一种现代表达方式,更能展现平常生活的诗意。评论者普遍认识到弗罗斯特将人们使用的话语变成了诗歌,认为在别的诗人笔下只能是日常琐事的故事素材,在弗罗斯特的诗中却因其朴实无华、真挚动人而具有了普遍意义。这一时期的评论使在英国寻找发展机会的弗罗斯特一举成名,并且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到美国时,受到了美国民众像对待英雄一样的欢迎。
美国民众将弗罗斯特视为本土英雄、理想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这使弗罗斯特在20世纪20年代比此前更为人瞩目。1927年,戈勒姆·穆森(Gorham B.Muson)的弗罗斯特诗歌研究专著《罗伯特·弗罗斯特:情感与理智研究》(Robert Frost:A Study in Sensibility and Good Sense,1927)对弗罗斯特的生平和诗歌创作技巧进行论述,指出弗罗斯特诗歌主题宏伟壮丽,但是他的诗歌语言却完全像日常对话。1938年,美国作家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在《星期六文学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上发表题为《批评家与弗罗斯特》(“The Critics and Robert Frost”)的文章,认为弗罗斯特是“一位伟大的美国诗人”,他“颠覆了美国诗歌中应该被颠覆的一些东西”。[3]1942年,劳伦斯·汤普森(Lawrance Thompson)在弗罗斯特诗歌研究专著《火与冰:弗罗斯特的艺术与思想》(Fire and Ice:The Art and Thought of Robert Frost)中认为,弗罗斯特的诗歌艺术牢牢地扎根于悠久的英诗传统之中,“在弗罗斯特微妙的诗歌表层结构之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诗人广泛而又娴熟的诗歌技巧应用,而且能够感受到诗人充满活力和理性的精神深度。”[4]这些评论对弗罗斯特的诗歌内容及创作技巧给予好评,但是面对政治形势的纷繁复杂,作家们在20世纪30年代纷纷趋向于成为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评论家们也以政治因素作为评判作家及其作品的重要准绳。此时,弗罗斯特却坚持保守的政治立场,不肯参加任何左翼或右翼运动,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无益于社会的群体性活动。这一政治立场引发了人们对弗罗斯特及其诗歌的批判。评论家们认为弗罗斯特是一个逃避主义者,他的传统价值观念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危险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率先在1930年12月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撰文攻击弗罗斯特,并且指出:“弗罗斯特不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属于这个工业的、科技的和弗洛伊德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找到自己。”[5]希克斯认为考察各个时期的文学成就需要考察作者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的关系,而弗罗斯特诗歌不能代表美国的社会生活,只能代表一种行将消逝的生活方式,让读者远离这个真实的世界。此后,有学者从道德批评的角度否定弗罗斯特诗歌的价值,或者在肯定弗罗斯特作为一流诗人的同时指出其作品的社会功能不足。在1937年弗罗斯特凭借《山外有山》这部诗集获得普利策奖之后,评论家们尤其是左翼政治思想家们纷纷在《新群众》(New Masses)和《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弗罗斯特。例如,马尔科姆·考利在1944年9月的《新共和》上发表题为《弗罗斯特:一点不同意见》(“Frost:A Dissenting Opinion”)的文章。考利认为,弗罗斯特的诗歌艺术及其致力于诗歌艺术的漫长生涯都无愧于他所获得的一切殊荣,但是一些热情的崇拜者没有实事求是地评价弗罗斯特及其诗歌,仅仅是把诗人当作他们进行一场道德和政治运动的旗号。考利也对人们把弗罗斯特称作新英格兰的代表表示质疑,认为诗人过分地沉溺于过去的历史之中,推崇一种古老、简朴和欢悦的生活方式而拒斥了现代性的诸多特征,“这位诗人依靠传统,不能令人信服,他更多关注的是谨慎的智慧而非杰出的美德,他几乎不关注罪恶和痛苦。”[6]弗罗斯特备受人们的称赞,享受各种荣誉,而考利等批评家们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弗罗斯特歌颂的是废弃的古董店,不应获得如此赞誉。
这一时期,诸多评论家们在报纸杂志上撰文,对弗罗斯特作出褒贬不一的评论。詹姆斯·考克斯(James M.Cox)在《罗伯特·弗罗斯特:一本批评文集》(Robert Fros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1962)中收录了新老评论家自1942年至1960年有关弗罗斯特的评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劳伦斯·汤普森的《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理论》(“Robert Frost's Theory of Poetry”)、马尔科姆·考利的《反对弗罗斯特先生的实例》(“The Case Against Mr.Frost”)、以伊沃尔·温特斯的《罗伯特·弗罗斯特:作为诗人的精神漂流者》(“Robert Frost:The Spiritual Drifter as Poet”)、莱昂内尔·特里林的《关于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次演讲:一件文化逸事》(“A Speech on Robert Frost:A Cultural Episode”)、乔治·尼奇(George Nitchie)的《遏制混乱的短暂片刻》(“A Momentary Stay against Confusion”)以及约翰·莱伦的《作为现代诗人的弗罗斯特》(“Frost as Modern Poet”)等。这些评论主要代表了两种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弗罗斯特是一个与时代和社会格格不入的逃避主义者,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弗罗斯特是一个关注时代的现代艺术家。考克斯则致力于展现有关弗罗斯特评论的全貌,经过对这些评论的归纳和分析,考克斯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迄今为止有关弗罗斯特的评论只达到两个阶段,即对诗人的认识与接受,而目前弗罗斯特诗歌的研究需要达到第三个阶段,即对诗人的全面理解与进一步发现。考克斯相信弗罗斯特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发现和确定弗罗斯特是如何通过其诗歌意象呈现出诗歌结构的:“在其诗歌世界中,人、诗人和诗歌是统一体。巧妙的设计揭示出诗人在言说诗歌,他的诗歌是一种游戏,这是他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这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神话。”[7]考克斯提醒评论者不应一味地贬低或者赞颂弗罗斯特的诗歌,而应该全面、深入地探讨弗罗斯特诗歌构建的神秘世界,找到弗罗斯特诗歌中的主要特性,这对后来的弗罗斯特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弗罗斯特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的兴盛时期。1961年1月20日,数千万美国大众通过电视媒介看到弗罗斯特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作的画面。随着弗罗斯特的名气达到鼎盛阶段,美国学术界也掀起有关其诗歌研究的热潮。这一时期,涌现大量运用社会批评、道德批评和形式批评方法,探究弗罗斯特诗歌的创作特点、主题思想、艺术源流等方面内容的著作。
评论者普遍关注弗罗斯特诗歌的艺术特点。例如,约翰·莱伦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牧歌艺术》(The Pastoral Art of Robert Frost,1960)一书中运用新批评方法突出研究弗罗斯特诗歌创作的独特性。作者结合弗罗斯特诗作中的叙述、音调、声音等要素,冷静、客观地分析其艺术风格,认为弗罗斯特对自然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理解,他不是一个栖居乡村的农民诗人,而是一个深奥微妙的艺术家,他最具代表性和最重要的作品都采用牧歌结构,将质朴简单的新英格兰乡村世界与现代城市世界作对比。作者进一步指出:“尽管他描述的是一片森林或者一丛野花,但是他作品的真正主题是人性。他在偏远的自然中揭示出人类面对孤独时的悲剧,以及面临巨大的、非个人化力量时的脆弱性。”[8]美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德·波瑞尔(Richard Poirier)的著作《罗伯特·弗罗斯特:智慧之作》(Robert Frost:The Work of Knowing,1977)更加受人瞩目。在这部当时堪称最全面、最客观地褒扬弗罗斯特及其诗作的著作中,作者没有过多关注其诗歌呈现的政治思想或社会问题,而是探讨《在一条山谷里》(“In a Vale”)和《梦中痛苦》(“A Dream Pang”)这些此前很少被人关注的诗歌,甚至挖掘弗罗斯特诗歌中的一些敏感因素,例如《下种》(“Putting in the Seed”)和《被骚扰的花》(“The Subverted Flower”)中所涉及的有关弗罗斯特细致入微的性描写话题。与此同时,作者结合英美文学背景以及20世纪的社会现实探讨弗罗斯特的诗作,并在与其他诗人诗作的比较中拓展弗罗斯特诗歌批评的视野,进而指出弗罗斯特的诗歌艺术是一个有机整体,代表了20世纪文学发展的方向。这一时期,学者们还探讨了弗罗斯特诗歌中有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上帝、人与科学和人与历史等方面的主题。例如瑞德克里弗·斯奎尔斯(Radcliffe Squires)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主题》(The Major Themes of Robert Frost,1963)一书中提出,弗罗斯特与其他现代派诗人一样关注人类社会,尤其关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通过作品呈现人类陷于各种矛盾冲突的现代处境,思考人类究竟应该面对工业文明的矛盾冲突,还是应该在工业文明之外寻觅一片宁静天地这一两难境地。与此同时,学者们探讨了弗罗斯特思想的艺术渊源。罗本·布若尔(Reuben Brower)撰写的《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的情意丛》(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Constellations of Intentions,1963)被公认为早期弗罗斯特研究中的一本佳作。为了更加深刻理解弗罗斯特的诗歌,以及诗人在广阔的诗歌世界中的地位,布若尔从形式与内容方面考察和挖掘那些能够汇聚成弗罗斯特诗歌思想感情的情意丛。布若尔在这部专著里指出,弗罗斯特在思想艺术方面主要受到爱默生、亨利·梭罗和威廉·詹姆斯等作家的影响,其中华兹华斯和爱默生对弗罗斯特的影响最为深远。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有关弗罗斯特生平的研究。伊丽莎白·萨金特(Elizabeth Shepley Sergeant)的传记作品《罗伯特·弗罗斯特:生存的考验》(Robert Frost:The Trial by Existence,1960)讲述这位受人爱戴的诗人弗罗斯特的一生。而作为弗罗斯特本人授权的官方传记作家,劳伦斯·汤普森洋洋洒洒地撰写了三卷弗罗斯特传记,依次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早年岁月:1874—1915》(Robert Frost:The Early Years 1874-1915,1966)、《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成功之年:1915—1938》(Robert Frost:The Years of Triumph 1915-1938,1970)以及在汤普森去世后由其学生威尼克(R.H.Winnick)遵照遗愿继续完成的第三卷《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晚年时光:1938—1963》(Robert Frost:The Later Years 1938-1963,1976)。但这三本传记材料冗杂,叙述平淡,对诗人的生活及性格轻描淡写,对其诗歌作品的评论矛盾重重,这些给读者带来巨大的震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弗罗斯特的诗人名声,遭到后来弗罗斯特传记作家的批评和质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弗罗斯特研究向着纵深方向发展,在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批评家们以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探讨弗罗斯特诗歌的内涵及特征,注重分析其诗歌的主题、意象和表现手法等文学因素;第二,研究者在探讨弗罗斯特诗歌理论的同时追溯其思想艺术渊源,尤其注重分析弗罗斯特对华兹华斯和爱默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第三,研究者往往从自身立场和主观理解来看待弗罗斯特及其诗歌,对弗罗斯特或批评或称赞,态度截然对立,这一时期的传记作品也有失客观。可以看出,这段时期的弗罗斯特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还留下很多研究空间,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弗罗斯特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之开辟了道路。
弗罗斯特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领域的拓展阶段。这一时期,弗罗斯特诗歌的艺术特征、思想渊源和诗人的生平研究依旧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
其中,研究者结合新的批评理论与研究成果,集中探讨弗罗斯特诗歌的艺术渊源。例如马里奥·达方佐(Mario D'Avanzo)在《罗伯特·弗罗斯特与浪漫主义诗人的相似性》(A Clouds of Other Poets:Robert Frost and the Romantics,1991)一书中,梳理了莎士比亚、爱默生、梭罗、华兹华斯、雪莱、柯勒律治和济慈等作家,以及古希腊文学、古罗马诗歌和《圣经》等经典文本对弗罗斯特诗歌创作的影响。结合弗罗斯特的书信、散文、谈话等资料,作者探讨了弗罗斯特诗歌中呈现的积极浪漫主义因素,并且指出:“在弗罗斯特诗学的形成过程中,他受到很多诗人和诗歌的影响。这些与现实中的纷繁混乱汇合在一起,构成弗罗斯特诗歌的独特风格。”[9]与20世纪60年代考察艺术渊源的研究成果相比,达方佐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华兹华斯和爱默生对弗罗斯特的影响,考察的视野更为广阔,并且结合具体诗作分析了弗罗斯特对前人艺术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弗罗斯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例如马克·理查森(Mark Richardson)在《罗伯特·弗罗斯特及其诗学的苦难历程》(The Ordeal of Robert Frost:The Poet and His Poetics,1997)一书里继承了美国文学史家范·布鲁克斯(Van Brooks)在其经典著作《马克·吐温的苦难历程》(The Ordeal of Mark Twain,1920)里率先采用的社会分析模式,将美国的现代诗学与文化批评结合起来。理查森认为,弗罗斯特诗歌风格的形成以及其关于诗学的论述,都受到诗人自身经历和所处社会的苦难历程的影响,而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又试图超越这些苦难,因此,读者“值得进一步将弗罗斯特界定为美国文学传统中的社会思想者”。[10]理查森进一步指出,弗罗斯特比作为精英文人的庞德更愿意取悦读者。弗罗斯特本人对诗歌节奏与韵律等技巧的选择除了与主题表达相关外,还与美国文化的女性化趋势、美国的文化消费市场走向以及诗人对自己所创作诗歌的定位等各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这种关于主题与艺术特征成因的探讨开拓了弗罗斯特诗歌研究的新思路,成为这个阶段学术界所取得的一个显著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将弗罗斯特的诗歌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有利于改变人们以往认为的弗罗斯特诗歌“过于简单”的成见,赋予弗罗斯特诗歌研究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一时期学术界在弗罗斯特生平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弗罗斯特传记作者重新审视和认识诗人,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以前传记中的错误,弥补以往有关研究的不足。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先后问世,杰伊·帕瑞尼(Jay Parini)的《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生》(Robert Frost:A Life,1999)尤为客观翔实,该书对汤普森的三卷本弗罗斯特传记作出公正的评论,认为该传记“毫无选择地堆积细节”,以至于把这位诗人写成了“一个恶魔似的人物”。[11]帕瑞尼撰写的弗罗斯特传记试图还原诗人的本来面目——他既非圣徒也非恶魔,而是一个囊括诸多内涵的活生生的人。尽管作者记述了弗罗斯特本人的一些缺点,但仍承认弗罗斯特作为伟大诗人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这部传记中客观地运用诗人的生平资料来分析诗人的诗歌作品,充分体现了传记研究的学术价值。
可以看出,这期间的弗罗斯特研究继承以前的研究成果,弥补其中的一些不足。研究者不再停留在罗列现象的层面上,而是深入探讨现象形成的原因,从聚焦于个案推广到着眼于整体的文学传统,对弗罗斯特诗歌与相关作品作出横向比较的尝试,使弗罗斯特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为21世纪弗罗斯特诗歌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为深厚的基础。
弗罗斯特研究的第四个阶段是2000年以后该领域取得突破的时期。这一时期弗罗斯特诗歌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一方面继承传统的文学研究思路,另一方面顺应当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地转向文化研究。
由《罗伯特·弗罗斯特评论》(Robert Frost Review)杂志创刊主编厄尔·威尔科克斯(Earl Wilcox)和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乔纳森·巴伦(Jonathan N.Barron)博士共同编辑的论文集《未走之路:重读罗伯特·弗罗斯特》(Roads not Taken:Rereading Robert Frost,2000)对弗罗斯特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部论文集中,马克·理查森的论文《冷战与弗罗斯特后期诗歌概观》(“Frost and the Cold War:A Look at the Later Poetry”)力图结合冷战这一文化背景来重新审视弗罗斯特的诗歌。乔纳森·巴伦在文章《两幢小屋的故事:弗罗斯特与华兹华斯》(“A Tale of Two Cottages:Frost and Wordsworth”)中指出,弗罗斯特的诗歌《黑色小屋》(“The Black Cottage”)继承华兹华斯《废弃的小屋》(“The Ruined Cottage”)中的写作风格,但是弗罗斯特立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文化背景,融入民族、宗教、政治等方面的内容,其诗歌具有更加丰富的意义。沃尔特·乔斯特(Walter Jost)的论文《弗罗斯特修辞研究》(“Rhetorical Investigations of Robert Frost”)则从修辞学和阐释学的角度认为,弗罗斯特对话式的诗歌是一场充满知性的革新,为美国民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部论文集视角独特,研究者通过关注弗罗斯特诗歌中较少有人提及的性别问题,阐释弗罗斯特诗歌中的文化背景,以及探讨弗罗斯特对诗学的革新,强调了弗罗斯特作为一位现代派诗人的地位。该论文集指出,人们在提及现代派诗人时往往津津乐道于庞德和艾略特诗歌的深奥玄妙,而忽视弗罗斯特对现代社会的独特理解,这为读者重新审视弗罗斯特的诗歌指明了方向。泰勒·霍夫曼(Tyler Hoffman)在其著作《罗伯特·弗罗斯特与诗歌政治》(Robert Frost and the Politics of Poetry,2001)中指出,弗罗斯特诗歌中的政治取向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诗人总是试图在其诗歌形式理论与诗歌的政治兴趣之间取得平衡。该书的作者还发现,弗罗斯特以其复杂的编码形式表达他的政治观点与文化身份,使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位诗人纳入当下意识形态与诗学政治中,对其进行具有创新性、富于成效的研究。约翰·蒂莫曼(John Timmer-man)在《罗伯特·弗罗斯特:暧昧的伦理学》(Robert Frost:The Ethics of Ambiguity,2002)一书中认为,弗罗斯特诗歌在表达意念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双重或多重意义,诗意暧昧不明。作者详细分析了弗罗斯特诗歌中的美学伦理、理性伦理、宗教伦理和社会伦理等,认为弗罗斯特的诗作被十分微妙地包裹在含混与朦胧的外衣之下,其中确实贯穿着颇为深邃的伦理思考。与此同时,史蒂文·弗雷塔利(Steven Frattali)在著作《人物、地点和世界:弗罗斯特的后现代解读》(Person,Place,and World:A Late-Modern Reading of Robert Frost,2002)中着重探讨诗人的哲学思想。作者指出,弗罗斯特阅读过法国现象学大师梅洛-庞帝和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泽的著作,其诗歌主题深受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影响。诗人将深奥的哲理诉诸形象的比喻,通过意象的无限展现来反映现实在绵延时间中的流变,进而表达诗人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刻理解。罗伯特·帕克(Robert Pack)在其专著《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的信仰与怀疑》(Belief and Uncertainty in 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2003)中以想象与现实、信仰与怀疑为主线,结合弗洛伊德理论和达尔文主义细读弗罗斯特诗歌文本。作者认为弗罗斯特相信信仰的巨大力量,同时在诗歌中又表达虚无的思想,弗罗斯特是一位存在主义诗人。作者还综述了自然与环境的生态观念,梳理自艾米莉·狄金森以来美国诗歌中的自然观。在此基础上,作者运用生态批评的方法分析弗罗斯特的自然诗作,进而指出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自然具有不确定性,既妩媚动人又对人构成威胁,在大自然当中美与毁灭共生,而自然超越人类的力量往往是诗人敬畏自然的原因。与此同时,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女性问题与生态主题是这一阶段研究的热点,学者们纷纷从精神分析、文化研究、女性研究和读者反应这些视角解读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主题,认为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女性都是一些遭受挫折的形象,充分体现了诗人作为男性的自信。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美国的弗罗斯特研究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其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全面,考察视角和所运用的方法也越来越新颖,充分展示弗罗斯特诗歌的研究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