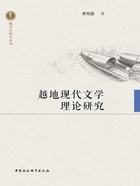
第二节 越地现代文学理论强调文艺的审美性
夏丏尊说:“人生是多元的,人的生活有若干的方面,故有若干的对象。知识生活的对象是‘真’,道德生活的对象是‘善’,艺术生活的对象是‘美’。我不如艺术派所说,相信‘美’与‘善’无关,是独立的东西,但亦不能承认人生派的主张,把‘美’只认为‘善’的奴仆。我相信文艺对人有用处,但不赞成把文艺流于浅薄的实用。”[61]“文艺的本质,是超越现实功利的美的情感,不是真的知识与善的教训,但情感不能无因而起,必有所缘。因了所缘,就附带有种种实质。或是关于善的,或是关于真的。我们不应因了这所附带的实质中有善或真的分子,就说文艺作品的本质是善的或是真的。”[62] 夏丏尊在这里像其他越地现代文学理论诸家一样,强调了文艺的审美性。
一 文学反映现实以审美为基础
徐懋庸在《风景描写》《心理描写》《再谈心理描写》《典型人物的描写》等文章中专门就风景描写、心理描写、典型人物的描写等具体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在《心理描写》中徐懋庸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显然是不完全的:“人类的欲望,不止一种性的欲望,受外界检察的,也不止一种性的欲望。在历来的社会里,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的愿望,都是受着社会制度的检察和抑制的。人类的苦闷,实系社会制度的矛盾反映而成,而且,人类的一切心理现象,都不是从个人心中凭空地发生,而是由社会的现实所决定的。”[63] 徐懋庸同夏丏尊一样,看到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所以,在对创作目的和动机等问题的解答上,徐懋庸体现了现实主义原则。在《“为谁而写作”》中他给出的答案是:“一个作家,有所写作,总是为了一切人或多数人。”[64] 他认为读者是创作的最终目的和动机。另外徐懋庸的现实主义原则强调艺术对于读者的精神影响。在《创作的态度》中他说:“凡有写作,当然是想获得读者的。但作家的获得读者,并不像娼妓获得狎客那样靠了媚悦的手段。作家是象传道者那样,用了自己的精神,去打动别人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作家是任性的,他只是表现自己所要表现的东西。”[65]
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考察,肯定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无疑是正确的出发点。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66] 但同是反映,在各个意识领域内,反映的方式和内涵是不同的,列宁在《哲学笔记》里就曾批评过那种把作为认识论原则的感觉和作为伦理学原则的感觉混淆起来的作法。文学不同于一般意识形态,它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反映,即审美反映。这种审美反映,不仅在反映形式上有别于科学反映,而且在掌握现实的方式上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正如夏丏尊所言,人生是多元的,人的生活有若干的方面,故有若干的对象。人生可以一分为三,知识生活、道德生活、艺术生活,与之相对应的对象分别是真、善、美。
夏丏尊的观点与马克思的思路是暗合的。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时,曾将科学认识与“对世界的精神的掌握”的其他形式区别开来:“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67]如果说,科学认识侧重于把握事物的性能,实践精神侧重于把握事物的功用,宗教是用对彼岸世界的幻想方式来把握此岸的现实世界,那么艺术认识则是对现实进行审美的观照。譬如,同是面对一座古塔,科学的认识是研究其建筑结构和材料性质,考察其经久不倒的原因;实践精神则研究其利用价值;宗教精神把它当作神灵的象征而顶礼膜拜,而且附会许多宗教传说;艺术方式的认识则是欣赏其苍劲挺拔的姿态,而在审美观照的过程中,早已移入了审美主体自己的感情,并从古塔的姿态中看到某种象征意义,联想到某种人间精神。这样,在审美观照中,就产生了某种意象,如果把它写入诗中、绘入画中,就是艺术的反映、审美的反映。因为有了这种意象的作用,艺术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已非客观现实本身,而是人化了的自然。[68]
二 越地现代文学理论强调现实是审美的基础
客观现实是创作的基础,是艺术反映的对象。没有这个对象,就无从认识,无从感知,无从反映。
尊重现实,强调作者多从观察现实、积累知识入手是徐懋庸一贯坚持的主张。他在《高尔基和香菱》中说:“一切作品都是他亲眼看见过的现实生活的记录。高尔基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是使他成为当代大文豪的最要紧的条件,这是毫无疑义的。现时代的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必须从充实生活、练习观察入手。”像香菱那样从书本到书本而忽视现实生活基础是不行的。[69]
但是,艺术的反映毕竟不是简单的模仿,不是镜子中的映象,不是照相底片上的感光,而是经过主观化了的客体,是主客观的统一。正如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他把图画看成是经过“艺术家的热情”滤过的一块自然,没有艺术家的这种热情,图画便不存在,是个空地方。[70] 类似的观点,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发表过不少,可见是人们共同的体验和共同的见解。
古罗马西塞罗说:“那位大雕塑家雕塑龙庇特神像或者米涅瓦神像的时候,他看的一定不是任何一个模特儿,他的心目中有一个绝世无双的美的形象,他注视的是这个形象。他照着这个形象,专心致志的指导他那双艺术家的手来塑造神的形状。”[71] 这就是说,雕塑家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来塑造神的形象的。西班牙现代画家毕加索说:“我注意到,绘画有自身的价值,不在于对事物的如实的描写。我问我自己,人们不能光画他所看到的东西,而必须首先要画出他对事物的认识。一幅画像表达它们的现象,那么同样能表达出事物的观念。”[72] 可见这位艺术大师是将现象和观念统一起来,作为绘画的对象的。
徐懋庸说作家是表现自己所要表现的东西,这种表现的结果显然不是客观现实本身。他说巴金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作家的意识是被生活所决定的。我的生活使我感到尚有猛烈地攻击黑暗之必要,我的生活给我太多的悲哀,所以我自然而然写出了那些作品,我不能故意地去写别样的作品。”[73]
这与古今中外文艺理论对作家反映现实具有能动性的认识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画家石涛有题画诗云:“名山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变幻神奇懵懂间,不似似之当下拜。心与峰期眼乍飞,笔游理斗使无碍。昔时曾踏最高巅,至今未了无声债。”[74] 这里所说的“心与峰期”“笔游理斗”,也就是指心物统一、情理结合的意思,所以画出来的山景不是逼真的写生,而是“变幻神奇”“不似似之”。后来齐白石所说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黄宾虹所谓“作画当以不似之似为真似”,都是这个意思。
关于自然之物与画中之物的关系,讲得更清楚的是郑板桥和潘天寿。郑板桥在题画中详细地描述了他的审美感受和艺术表现的过程:“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75] 这里,画家明确地将眼中之竹(实物)与胸中之竹(意象)区分开来。胸中之竹虽然来自眼中之竹,但经过审美观照,融入胸中勃勃的情意,已非原来眼中之竹了;而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倏作变相”,画出来的竹又非胸中之竹,更变了一层。潘天寿说:“画中之形色,孕育于自然之形色;然画中之形色,又非自然之形色也。画中之理法,孕育于自然之理法;然自然之理法,又非画中之理法也。因画为心源之文,有别于自然之文也。故张文通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76] 这是艺术家从自己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他认为画中之形色既来源于自然之形色,又不同于自然之形色,而且明确地意识到,它已加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成分,即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心物的统一。关于心物统一的境界,说得更神妙的还是石涛。他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77]
这种心物统一的过程,就是所谓“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实践观点还只是萌芽状态,那么,到了马克思手里,便得到进一步的发挥。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主要是指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外化到劳动对象上去。这一点,他在《资本论》中谈得很清楚:“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会通过劳动手段,而在劳动对象上引起一个预先企图的变化。……劳动和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了。劳动是物质化在对象中了,对象是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表现为动作的东西,在产品方面,是当作静止的属性,表现在存在的形式上。”[78] 但马克思并没有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局限在物质生产中,他同样用这种理论来分析精神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说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物质生产,或者精神生产,人总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的。因而,艺术家所反映的世界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自然,而是经过审美改造、外化了人的本质力量的那个自然。所以,夏丏尊强调文艺作品所描写的自然人生是通过了“作家的心眼”的自然人生,许钦文认为发泄在文学上面的苦闷并不是作者直接的诉苦,是用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三 “神与物游”体现了审美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神与物游”。如何做到“神与物游”?在刘勰看来,作家的“志气”——思想感情和个人的生命力——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制约“神”——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关键。刘勰明确指出了培养“志气”的具体方式:“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79] 范文澜注曰:
此四语极有伦序。虚静之至,心乃空明。于是禀经酌纬,追骚稽史,贯穿百氏,泛滥众体,巨鼎细珠,莫非珍宝,然圣经之外,后世撰述,每杂邪曲,宜斟酌于周孔之理,辨析于毫厘之间,才富而正,始称妙才。才既富矣,理既明矣,而理之蓄蕴,穷深极高,非浅测所得尽,故精研积阅(阅有积历之意。研,磨也,审也,有精思渐得之意。)以穷其幽微。及其耳目有沿,将发辞令,理潜胸臆,自然感应。若关键方塞而苦欲搜索,所谓理翳翳而愈状,思乙乙其若抽,伤神劳情,岂复中用。怿疑当作绎,绎,抽也,谓神理之至,须顺自然,不可勉强也。[80]
范文澜的注释进一步解释了“神与物游”体现的再现与表现相统一的特征。在文学创作实践中,“神与物游”是通过自我情感和对象情感的相互冲突、相互搏斗、相互征服、相互突进而实现的。如同已故当代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对此的解释:
一方面是作家的灵魂突进对象,从而体验到对象的活跃的情感激流,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是对象的灵魂突进到作家的情感世界,从而在作家的主体里,扩大了与对象相适应的情感因素,克服与对象不适应的情感因素,使作家的情感世界重新分解与再度建构,填补作家原有情感建构的缺陷。[81]
这样看来,把艺术看作简单的客体再现或纯主体的自我表现,都不能说明它的本质。只有将再现和表现统一起来,才能解释艺术现象的复杂性。
许钦文由此看到了作家表现生活与生活本身的区别,他说:“现代的文学,作者总是有着对于所写事实以外的一种用意的。即使所写的故事原是真的事迹,也只是偶然得用;总之是利用事实,并非为着事实服务。”[82] 夏丏尊既强调文艺的本质是超越现实功利的美的情感,又强调情感必有所缘,尤其是现实根源。越地现代文学理论把审美看作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的观点,是对历史的回应。
我国古代《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83] 这就是说,音乐是人的主观情感的表现,而这种情感则是由外界客观现实所激发起来的。这种解释,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当然也有直接描写现实景象、模仿生活音响的乐章,如琵琶曲《十面埋伏》中描写军旅之声,二胡曲《空山鸟语》中模仿鸟鸣之声;而更多的乐曲并不直接再现生活景象,而是表现某种情绪和感情。与其说二胡曲《二泉映月》是再现无锡惠泉的月夜景色,倒不如说它是表现一个贫苦艺人在此情此景中所激起的哀怨之情。即使在上述描写性的乐章里,也不是单纯地模仿,而是充满感情地描摹。
不但音乐如此,在其他艺术领域里,也总是再现和表现的统一、描写与抒情的结合。法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说:“即使在画人体习作时,感情的表达也应该放在第一位。”[84] 我国近代画家黄宾虹说:“山水画乃写自然之性,亦写吾人之心。”[85] 有些评论家常以“酷似”“乱真”为赞语,其实“酷似”“乱真”并非艺术的上乘,如果仅仅做到“酷似”“乱真”,只不过是匠人之作,这就是苏东坡所讥评的:“作画求形似,见与儿童邻。”真正的艺术作品要在描写中透出灵气,即黑格尔所谓“灌注生气”。《张大千传》中记载有一蜀中老者来找张大千鉴定他的画。此老数十年如一日,专心作画,耗尽家财,遭到家人反对,而矢志不移。但他的画只求形似,毫无生气。譬如,他画蝴蝶,就收购了许多蝴蝶,刻意临摹,画得相当逼真,但可惜类似标本,并非艺术作品。这是从根本上把路子走错了,张大千只好安慰他几句完事儿。这种错误的画法,并非鲜见,宋代画家文与可就曾批评这种机械模仿的画法道:“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也。自蜩蝮蛇 ,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而他自己的经验则是:“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86] 所谓“成竹在胸”,就是对描写对象有一个完整的审美观照,这胸中之竹就寄寓着画家自己的主观精神,有似活物,稍纵即逝。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有神,有无成竹,尚在其次。郑板桥就唱过反调:“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俱足也。”不过他接着就说:“然有成竹无成竹,其实只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神理俱足”。[87]
,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而他自己的经验则是:“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86] 所谓“成竹在胸”,就是对描写对象有一个完整的审美观照,这胸中之竹就寄寓着画家自己的主观精神,有似活物,稍纵即逝。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有神,有无成竹,尚在其次。郑板桥就唱过反调:“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俱足也。”不过他接着就说:“然有成竹无成竹,其实只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神理俱足”。[87]
艺术创作如果只讲再现,而不讲表现,就会显得机械、呆板,缺乏神理,缺乏灌注生气。反之,如果只讲表现,不讲再现,那也会脱离现实。事实上,自我的感情总是与现实相联系,由现实状况激发起来的,而且也总是通过物象表现出来的,所谓托物寄情是也。即使如倪云林所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88] 确实随意极了,飘逸极了,但其实仍脱离不了现实。首先,他这飘逸之气还是现实社会所造成的;其次,这种飘逸之气也还是要借几笔竹枝之类表达出来。
因此,尽管各种艺术类型和艺术流派的侧重点不同,有的重在再现,有的重在表现,但是,完全摆脱某一种因素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来,总是再现中有表现,表现中有再现,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再现与表现是文学艺术中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巴尔扎克说:“作者希望,如果他说:‘文学艺术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观察和表现所组成的。’希望这句话符合每一个有识之士(包括智力高的或智力低的)的看法。”[89] 十分强调观察的左拉也说:“然而,观察并不等于一切,还得要表现。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真实感以外还要有作家的个人特色。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应该既有真实感也有个性表现。”[90]
总之,艺术创作是再现与表现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而其结合点,就是人对现实的审美观照。正是通过审美的观照,主体与客体才可以统一。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审美的特点来把握文学艺术的本质。而对这种艺术本质的把握反过来又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徐懋庸在《偶然做做或拼命去做》中说:“所谓拼命去做,是把文艺当作自己的性命,把文艺和生活看作二而一。为了发展自己的艺术,便拼命发展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发展到最高度,艺术也自然而然地发展到最高度。”[91] 他还认为,文学家除了要有生活经验,要读书籍,还要有对于真善美的爱。“这种爱当然不是个人的自私的爱,是爱大众的真理,爱大众的正义,爱大众的美满光明的爱,是新的人道主义的爱。”[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