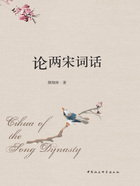
导论
一 两宋词话的理论形态
1.艺术生产
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结构的自由象征,是人类对世界和对自我的想象性的直觉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将文艺规定为意识形态的存在之一,视之为社会存在的审美反映。它一方面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视角对艺术进行阐释,马克思又提出“艺术生产”[1]的概念,强调文艺的实践性和生产性,将艺术生产视为人类精神对世界和对自我的一种特殊的把握方式,这就是审美的或想象的把握。宋词,也属于“艺术生产”的精神果实。而“词话”,这种与词相联系的文本样式,则作为对词的“理论把握”的存在形式。
我们从“艺术生产”这个观念出发,简略考察两宋词话的历史文化背景,试图获得对两宋词话的理论形态的初步认识。
词的产生一方面属于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客观的社会历史的产物;另一方面属于精神存在的审美创造,是主观心灵的想象化的符号活动,既是人类精神的价值实现过程,也是含蕴教益的自我娱乐的文化形式。词,从“艺术生产”的理论意义上讲,它呈现为社会历史的精神文化产品,是社会实践和精神创造的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
从词的艺术生产的审美特征看,词是文学与音乐相融合的艺术结果,是以文学为主体、以音乐为辅佐的艺术形式。词,由于按曲歌唱,“依曲拍为句”,又称“曲子词”。另外,尚有“倚声”“乐府”“长短句”等名。词是隋唐燕乐兴盛而造成的客观的艺术产品,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说《诗经》时代,诗歌与音乐就建立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那么,词这种文体形式不过是这种联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燕乐,作为隋唐时期的新兴的音乐形式,与诗歌形式融合后,最终诞生词这一新型文学样式。《隋书·音乐志》云: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
至唐太宗时,燕乐发展至十部之多,《宋史·乐志》云:
一曰燕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
另外,唐代的“教坊曲”在开元、天宝年间就达三百余首,它们也是唐五代词调的重要来源之一。王灼《碧鸡漫志》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张炎《词源》认为:“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有关词的起源和发展,当然有诸多的因素起作用,但隋唐燕乐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宋词的艺术生产,无疑遵循了音乐与文学相融合的一般艺术规律,只是宋词的审美形式,比以往文学形式具有更严谨而完善的音韵格律。到了温庭筠时期,词已发展为精致的审美形式。至南宋时期,形成以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为代表的格律派。从社会功能来考察,词广泛地介入世俗生活,以现实内容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密切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另一方面,词在两宋作为一种文化潮流,成为最普遍的文化样式和社会交往媒介,是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之一。词,也体现了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结合,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所以,两宋以“词”作为文化的价值核心之一和重要的审美形式之一。两宋词家的高手迭出和绝妙佳作的不断呈现,构成其历史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美学景观,艺术生产的繁荣和经济发展表现为相平衡的比例关系。
2.理论把握
两宋词话正是对在上述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艺术生产的客观结果所展开的描述与评价。
所谓“词话”,从文体形态上说,由诗话演变而来,是针对词这种文学形式所进行的审美批评。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诗话,而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则被认为是最古之词话。从发展形态上看,早期的诗话与词话,并非是理论形态的著述。在写作动机上,写作者并未有意识地将之上升成为严格的理论模式,甚至也不确立什么逻辑概念或美学范畴,其目的只是资闲谈和供消遣,随意和即兴地就诗词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往往闪烁着思想火花和包含着审美悟性。在写作方式上,采取短小灵活、叙议结合的形式,多涉及诗词的创作“本事”以及具体的修辞技巧方面的问题,表述上一般舍弃抽象的思辨和逻辑的推导,当然也不追求理论的系统性。
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诗话与词话逐渐有意识地向理论形态过渡,写作者经过缜密的理论思考,系统地、深入地阐述相关的美学问题,并着重从艺术概念和逻辑范畴上进行探索,尝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如诗话,有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等。如词话,则有王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炎的《词源》等。这些诗话与词话,和前期的诗话与词话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一方面是理论上的自觉,有意识地向美学理论或艺术理论的高水平的思维境界靠拢,另一方面是尝试建立自我的逻辑起点、核心概念、理论体系,力图将诗词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两宋词话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是这样的性质,经历了从现象描述到经验评价、再从经验评价到理论建构的发展过程,这也是两宋词话的“理论把握”的逻辑序列。
如果说理论存在是以客观现象为对象的逻辑归纳,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方式对现象进行描述、分析、总结、概括,以达到某种规律性的认识。那么,两宋词话作为这样的理论存在还有一个逻辑发展的过程,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理论存在方式。
描述性的理论存在方式。两宋词话受诗话的影响而生成,如果说作为最早的诗话——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始于熙宁四年(1071),而最早的词话——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大约作于元丰初年(1078—1081),梁启超称为“最古之词话”。初期词话,作为一种词的评论样式,体现出随意自由和灵活多变的批评特点,它关注对艺术现象进行具体的描述和评点,如注重对“本事”的实证性考察,对艳情“故实”投入过多的兴趣,等等。如从北宋时期的吴处厚词话、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陈师道词话,到南宋初期的杨湜的《古今词话》、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等,这些词话在不同程度上局限于对具体现象的描述而忽略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抽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词话正是以其描述性的存在方式呈现了自身的特色,在对词的创作题材、创作动因、生活内容、审美趣味、艺术技巧、文字修辞等方面的描述过程中,融入了批评者的主观评价。因为“描述”的方式也属于理论的存在方式之一,所以,词话的“描述”性的理论把握构成了它的基本存在特征之一。
经验式的印象性批评。两宋的前期词话侧重于主观经验的印象性批评,对词家与词作的评价倾向于体验式的评论。这种评论虽然在理论把握上有时存在主观性太强的局限,但由于评论者大多具有丰富的艺术经验和审美鉴赏能力,基本上都能对所评对象作出切合实际的批评,甚至有诸多的审美发现。尽管有些批评更多从主观视界阐释文本和评说词家,以汉儒解经的方式去理解文本,采取想象性再创的释义方式诠解词家词作,如杨湜、鲖阳居士等人对苏轼及其词作的阐释,由于对文本采取了超越作者原意的理解,难免有些误读或曲解。但从总体上看,两宋词话的这种经验式的印象性批评呈现为对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诗化批评”形式的继承和发展,以感悟式的审美发现将词作内在的艺术精神和美学风貌揭示出来,虽然不是以诗论诗或以诗论词,但在对词的领悟过程中体现了空灵超越、自由洒脱的诗性精神,使理论把握的形式上升到新的境界,显示了两宋词话所达到的较高水准。如陈师道、鲖阳居士、王灼、胡仔、张侃等人的词话就具有这样的性质。
思辨性的理论提升。两宋词话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以王灼的《碧鸡漫志》为标志,初步显示了词话这个理论形态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碧鸡漫志》从对现象的描述走向理论的抽象和概括,系统地考察了词的起源论和词的艺术本体论的问题,提出“性情”“自然”“中正”“雅”等词的审美范畴和审美标准,并建立了词的批评的方法论。其后的胡仔,对词的结构美和整体美、意境美和形式美等问题也进行了较系统的理论研究,注重从逻辑思辨的角度去阐释问题,标志着词话的理论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和张炎的《词源》为代表,分别体现出两宋词话的理论发展倾向。前者侧重对艺术技巧的探讨,贯穿结构主义的方法和观念,重视对语言修辞方法的研究,使理论研究深入更为具体的层面,对词的创作和欣赏有了更为深刻精湛的认识。后者以一整套的哲学思辨的方法论进行词的音律、曲调、创作、欣赏等方面的分析、研究,确立自我的中心概念和基本范畴,由此建构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得出众多的审美发现,成为影响后世的词学理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