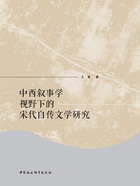
第二节 “六一”的“元叙事信号”功能与意象妙用的结构之技
“六一”在欧阳修自传中是一个饱含深意的文化意象,是欧阳修绝无仅有的独特艺术创造,它包含着欧阳修充实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对应物和投射物,也包含着欧阳修的“自我”本身,“六一”的命名令这个特殊意象具有了外物与自我既聚合又发散的矛盾特性,这种不确定的深刻的美感,为其赋予了难以比拟的艺术魅力。
在西方叙事学中,有“元叙事信号”这一概念,美国叙事学研究专家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对其功能进行探讨时曾这样写道:“最明显的元叙事信号——但未必是最大量和最重要的——也许是那些论及意素符码单位的信号。……叙述者还可能解释他所用词汇中的某一要素,因为他是以特殊方式来运用它的”[26],“给定任何叙事段落,元叙事信号能够表明其在一系列符码中的作用。它们也可以解释其语言的、社会文化的或符号的意义。它们能指出一定行为或事件状态代表着一个谜团或该谜团之破解……元叙事信号也能显示一系列事件属于同一情节序列而且它们可以为这一序列命名”。[27]以这一概念来观照欧阳修的自传《六一居士传》,其中,最能彰显其雅趣和人格追求的五件事物加上其自身——这“六一”就是明显的元叙事信号,因为欧阳修正是以“特殊方式来运用它的”[28],每一个“一”都自有所指,伴随着题目本身对读者好奇心和探究欲的激发,后文中对每一个“一”的解释都“代表着一个谜团或该谜团之破解”,并且随着后文中明示的“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29],元叙事信号“六一”也就充分显示了“一系列事件属于同一情节序列而且它们可以为这一序列命名”的特征。
因而,《六一居士传》的叙事模式可以说是“时而诉诸叙事性分析,时而采用我们或可称之为实体对应物(physical correlatives)的方式去象征性地表现人物的思想状态。”[30]而“六一”除了作为元叙事信号,同时还作为特殊意象的设置也充分体现了欧阳修高超的叙事技巧和谋篇布局的精巧构思,即“通过……其他实体物件来象征……思想状态,这样便能够依照自己所构想的意象去表现……内心世界,不至于因为过多地依赖叙事性分析而阻碍叙事的晓畅,或是让……思想语言受到修辞的强化和扭曲。”[31]“其构思旨在使那些象征能够履行某些人物塑造的职责,从而减少原本对叙事性分析或内心独白所提出的更高要求。”[32]
“六一”的丰富内涵,将欧阳修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人格认知都浓缩在了这两个字里,将原本需要长篇大论来讲述的人生经历和人格追求融会在这两个象征数字的文字中,以西方叙事学理论来加以观照,《六一居士传》呈现出高超的叙事技巧。“六一”作为元叙事信号的设置,不仅完美地履行了其应有的功能,而且从意象运用的视角考察,更是运思高妙的所在。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数字本身作为独特的象征符号代表了宏大的意义世界,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对于叙事文学中“数字”的运用有着如下妙论:“由于原始信仰和术数之学的影响,某些特殊的数字是指向宇宙玄机的神秘感的,它们的采用往往增添了一种哲理意蕴,或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因而可以和结构之道相通。但是,数字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排列顺序和数量组合的作用,因而一些数字的采用,又具有强化叙事顺序感,或强化叙事单元的组合力度的功能,由此又使它们与结构之技结下不解之缘。”[33]“六一”的运用,就令《六一居士传》呈现出了高超的结构之技。“一”这个数字作为宇宙万物原初的象征意义是源远流长的,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为这一认知奠下了哲思传统,“一”则成为了“道”的产物;而在其作为宇宙万物原初状态的象征意义之外,“一”还意味着某种超世独立、无与伦比的孤绝;而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则又体现了道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融为一体的思想。可以说,欧阳修的六个“一”中的前五个“一”,正是前两种象征意义的交融,而第六个“一”——“自我”的加入,则是第三种象征意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六一”这一意象设置的最终旨归。
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这样分析叙事类作品中意象的功能:“意象作为‘文眼’,它具有凝聚意义、凝聚精神的功能。……因而在意象别有意味地渗透于行文之时,意象可以作为意义的聚光点、意义的蓄水池,对作品的意义渗透进行有散有聚的调节,形成意义的聚散分合的体制。”[34]“意义一经凝聚。就会变得突出、集中和鲜明,积蓄为浓郁的审美滋味或强烈的审美撞击力。尤其是那些独特的、不同凡响的意象,往往可以增强心理震撼的叙事力度。”[35]而“六一”这欧阳修独创的、只属于他的意象,渗透于《六一居士传》全文,无疑是具有贯穿始终、凝聚意义的向心力,在欧阳修执意致仕、远离官场的思想的统摄下,五个象征作者高标雅趣和精神追求的“一”从行文开头与作者“自我”聚集合为“六一”,这六个“一”其实是一个整体,即成为了一个“物我合一的存在”;到结尾处,欧阳修袒露心迹,道明“吾负三宜去,虽无五物,其去宜矣,复何道哉!”[36]又将五个“一”作为相对自己的人格追求和精神自由而言的身外之物,将“自我”与其他五个“一”脱离,终于将“六一”意象在叙事上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自我”与其他五个“一”从开头的合而为一形成整体性的“六一”,到结尾处的离散,“我”与“物”的时聚时散,由聚至散,显示了欧阳修妙用意象的卓越叙事技巧。
除了运用“六一”意象的聚散来实现其作为“元叙事信号”和“特殊意象”对于整体行文叙事起承转合,意义勾连的草蛇灰线之外,欧阳修对主客问答这一叙事模式的设置亦是别具深意,其间蕴含着鲜明的价值判断。“元叙事信号倾向于揭示给定叙述者如何看待他面对的受众的知识与世故。他感觉必须要提供的元叙事解释,与他在提供这些叙事解释时所表露出来的老练程度,显示着他如何看待他的受述者,他是否尊重他们,是否对他们有好感,是否觉得自己有极大优越感。这些解释的分配,可能意味着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例如:如果叙述者停止进行元语言的陈述,那可能是因为他理解到他的受众不需要它们。”[37]
在《六一居士传》中,从“六一居士”开始回答客人提问时的风趣幽默,到中间的历练沧桑,深刻剖白,再到之后主动终止对话,“于是与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区区不足较也’”[38],欧阳修与他所设置的“客人”这一形象所代表的尖刻中满含审视和质疑的世俗心态在重重交锋后彻底背离,因而绝尘而去,不予作答。六一居士作为叙述者对于元语言陈述的主动停止,恰恰是“他理解到他的受众不需要他们”,因而,从开始时的认真作答,努力辨明,到主动结束对话。对话的终止,意味着主与客从并置走向了背离。欧阳修对于人生之“乐”的价值取向就在二者对话的开始—推进—终止中得到了有力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