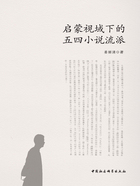
绪论
第一节 启蒙的概念辨析
1783年12月,德国的《柏林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一位名为约翰·弗里德里希·策尔纳的神学家和教育改革家所著,是探讨婚姻仪式根据民法来规定的可取性,这篇看似普通的文章却因注脚中的一个问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什么是启蒙?这个就像什么是真理一样重要的问题,在一个人开始启蒙之前就应该得到回答!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它已经被回答!”[1]这个问题并没有悬置太长时间,一年之内,《柏林月刊》就刊登了摩西·门德尔松和伊曼纽尔·康德的著名回答,使这一问题的答案得以深入人心。因此,尽管启蒙运动发源于英格兰与法国,但对启蒙这一问题首先进行深入思考的,却是德国。由是观之,“启蒙”一词有着纯正的欧洲血统,但这一词汇及那场以此命名的运动传入中国后,我们却发现它与中国传统中的启蒙定义有所不同。
在欧洲的主要语种中,都有“启蒙”这一词汇。在法语中对应的是Lumieres,在英语中对应的是Enlightenment,在德语中对应的是Aufklärung,在意大利语中对应的是Illuministi。这些词的基本意思是相通的,都指用“光”来照亮整个世界。当然,这个“光”的来源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意义。从古希腊的朴素人本主义哲学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从文艺复兴真正的“人本主义”到启蒙理性,这些思想资源都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照亮人类自身局限、使人类走向光明与自由的光源。18世纪,“在《关于解释自然的思想》中,狄德罗曾经把科学比做广大无边的大地,有的地方是明亮的,有的地方是晦暗的。‘我们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扩展光明的地带。’可见在狄德罗那里,‘启蒙’起源于‘光明’的隐喻,且具有百科知识的含义。这里最重要的是新的观察知识的角度,有一个启蒙的光源”[2]。另外,从词源学上考察,英文中,lighten的词根基本含义是“使……明亮”,enlighten意味着人通过受到启发进而脱离无知、偏见和迷信的境地,也就是后来18世纪启蒙运动中常常强调的“祛魅”作用——启蒙者认为,哲学、科学、文艺等各个领域在那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代表了“光”,可以用它的光辉去照亮宗教与封建制度加之于人们的蒙昧与迷信,所以以它命名的运动成为全欧洲的思想运动。这一词汇在西方现代语言中使用得非常广泛,说明这一概念的深入人心。“启蒙”在西方不仅是个充满争议的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给文学主题带来了全新变化的文学命题,更是给以欧洲为主的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的实践命题。
在欧洲“启蒙”概念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词汇中也有“启蒙”一词。但由于文化土壤的巨大差异,中国古代对于“启蒙”一词的使用与西方“启蒙”概念的上述两层含义有着一定的差别。在甲骨文中,“启”与“蒙”均为会意字。 “启”的甲骨文字形左边是
“启”的甲骨文字形左边是 (又),右边是
(又),右边是 (户,小门),“右手打开门户之形”[3];而“蒙”的甲骨文字形
(户,小门),“右手打开门户之形”[3];而“蒙”的甲骨文字形 是上面(将帽子套在头上)加下面
是上面(将帽子套在头上)加下面 (小鸟)组成,本义是“覆也”[4],也就是以帽子罩住小鸟。在甲骨文中,“启”与“蒙”是两个独立的会意字,各自使用,未组合在一起。最早将这两个字组合成词的是汉应劭《风俗通·黄霸·六国》中:“每辄挫衄,亦足以祛蔽启蒙矣。”[5]意为从挫折和失败中也能得到启发、教益。这里的启蒙即是启发、开导,指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的意思。这一启蒙概念强调的是“事理”,亦即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强调的“纲常伦理”,偏重的是社会教化作用。启蒙的第二层意思元朝刘壎《隐居通议·论悟二》中可见:“儿童初学蒙昧未开,故瞢然无知。及既得师启蒙,便能读书认字。”[6]这里的“蒙”指的是年幼无知的儿童的童蒙,而“启蒙”在这里意即使初学者学习到基本的入门知识,这一层意思多用于少儿教育方面,后来亦引申为通过宣传使社会能够接受新事物之意。
(小鸟)组成,本义是“覆也”[4],也就是以帽子罩住小鸟。在甲骨文中,“启”与“蒙”是两个独立的会意字,各自使用,未组合在一起。最早将这两个字组合成词的是汉应劭《风俗通·黄霸·六国》中:“每辄挫衄,亦足以祛蔽启蒙矣。”[5]意为从挫折和失败中也能得到启发、教益。这里的启蒙即是启发、开导,指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的意思。这一启蒙概念强调的是“事理”,亦即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强调的“纲常伦理”,偏重的是社会教化作用。启蒙的第二层意思元朝刘壎《隐居通议·论悟二》中可见:“儿童初学蒙昧未开,故瞢然无知。及既得师启蒙,便能读书认字。”[6]这里的“蒙”指的是年幼无知的儿童的童蒙,而“启蒙”在这里意即使初学者学习到基本的入门知识,这一层意思多用于少儿教育方面,后来亦引申为通过宣传使社会能够接受新事物之意。
启蒙的第一层含义蕴含的“启发、开导”之意,在中国近代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在王夫之的《周易外传》中有对“启蒙”一词的使用,但意思还比较模糊,未对概念进行明确界定。近代明确使用“启蒙”一词较早的是梁启超,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把清代学术分成“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与“衰落期”四个时期来进行研究。他认为启蒙期的特点即在于对旧思潮的反动,并认为启蒙的两大特点为“批判性”与“建设性”。这种概念发展到五四时期,渐渐自五四启蒙先驱的笔下出现,意思却与西方启蒙内涵相去甚远。五四时期,“启蒙”一词最早明确出现是在鲁迅笔下。在《连环图画琐谈》中鲁迅说:“借图画以启蒙”[7];《答曹聚仁先生信》中说:“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8]《门外文谈》中又说:“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所以,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9]这均是沿用了中国古代“启蒙”一词的基本含义。到了沈从文,这一概念也未有更多变化,他于1933年讲述一则古代故事,说它的作用是“为后世启蒙发愚之用”[10],并将孙俍工编写的《新诗作法》《散文作法》《小说作法》等示范参考的书称为“启蒙书”。上述二人对“启蒙”概念的使用都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启蒙”内涵——“启发”“开导”。相对而言,稍有些接近西方启蒙含义的是郁达夫。他曾说:“文艺批评在天才眼里,虽没有什么价值,在庸人的堆里,究竟是启蒙的指针。”[11]这里的“启蒙”便有了些“祛魅”的意味。进而,郁达夫在批判文坛上的浅薄风气时又说:“虽是在启蒙时代所难免的,但也须有一个限制才好。”[12]这种“启蒙”的概念,已有接近西方内涵的自觉。真正在西方启蒙内涵的范畴之内使用的,是郁达夫在向中国读者介绍影响赫尔岑思想的人物时,特别提到了“尤以法国启蒙哲学家和百科辞典编纂诸家如提特洛(狄德罗)、达兰倍尔(达朗贝尔)辈的感化为最深”[13],且介绍18世纪法国小说家时提到狄德罗与卢梭均以“启蒙哲学者”称之。这虽然只是作为介绍西方文学发展成就时的一种直译,并没有深究其内涵或是真正使用,但毕竟较之鲁迅、沈从文等人已经有所进步。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五四先驱开始把“启蒙”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及主义来使用。最先用到这层含义的是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4]这里鲁迅虽然没有明确地解释“启蒙”的内涵,而其“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文学主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近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些定义,当然与真正的西方启蒙内涵仍有差距。不过,由于当时五四启蒙先驱对于西方启蒙运动的理解与推崇还没有发展到明确与自觉的程度,因而在介绍西方的文艺运动及文学思潮时常常推崇文艺复兴运动及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而忽略18世纪启蒙文学思潮,甚至一度认为并不存在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这种现象直到“新启蒙运动”[15]开始后才发生根本转变,“启蒙”开始成为人们的自觉,这一口号广泛流行起来。
再从中国“启蒙”概念的第二层含义来看。《周易》里有“蒙以养正”的说法,可见启蒙的第二层含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得到了充分认识。而蒙学在古代是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的,徐梓在《中国传统蒙学述评》中指出:“二十岁以上的成人在农闲时节,到私塾或村学中接受启蒙教育的极其普遍。”[16]这说明除儿童外,蒙昧的成年人也在传统蒙学启蒙之列。因此这里启蒙对象的要件不是“儿童”,而是“蒙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启蒙对象之广泛。中国古代的启蒙不仅年龄限制宽泛,内容也颇有不同。在初步形成蒙学规模的明代,蒙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侧重纲常伦理教化的内容,清代蒙学情况基本与此相同。可见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文化普及与伦理教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在中国的两层意义殊途同归,都指向了伦理教化,这是迥异于西方启蒙的基本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