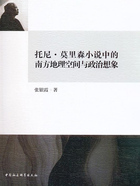
二 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阐述
1.托尼·莫里森研究述评
莫里森自20世纪70年代创作起就因其突出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创作风格而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热情随着作家在国内数次获奖和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而持续高涨。在其创作的同时,莫里森多次受邀进行访谈和讲座,这些资料都被整理成册出版,或者收录于各类访谈集及相关书籍中。学界对莫里森的研究也呈现出经久不衰的态势。
莫里森初登文坛就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所罗门之歌》出版前后。在非裔作家中,斯坦利·克劳奇(Stanley Crouch)把《宠儿》视为一部旨在迎合“感情用事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闹剧,说莫里森“缺乏真正的悲剧意识”,未能勇敢地面对“超越了种族的人类灵魂的善恶含混性”。[14]并且以克劳奇为代表的部分评论家在莫里森获奖后发表评论说,她获奖是因为“政治正确”,是对一个来自边缘,但是迎合主流文化趣味的作家的褒奖,是由于她背弃自己作为黑人作家的文化之根而采用欧洲小说模式进行创作的结果[15];而以林登·皮奇(Linden Peach)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莫里森的创作不仅挑战了对黑人文化和民族的传统理解,而且挑战了小说的本质及其潜能。[16]
早期评论主要集中在莫里森与女性主义方面。由于《最蓝的眼睛》和《秀拉》写到了女性的成长历程,所以此时的评论多关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价值观等方面。芭芭拉·克里斯琴(Barbara Christian)在《黑人女性小说家:一个传统的发展》(Black Women Novelists: The Development of A Tradition,1892—1976)中总结了1970年前的女性形象:“专横,喜剧化的妈咪形象;混血儿形象及混合种族的妇女,其生命必须是悲剧的;撒菲勒(Sapphire)形象,她主宰并阉割了黑人男性。”[17]评论认为莫里森的创作,尤其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有所突破,强调黑人女性的友谊和文化。其后,相对重要的研究有马乔里·普赖斯与霍顿斯·斯皮勒斯(Marjorie Pryse and Hortense Spillers)共同编辑的《魔术:黑人妇女、小说与文学传统》(Conjuring: Black Women,Fiction and Literary Tradition,1985),苏珊·威利斯(Susan Willis)的《特定化:黑人女性书写美国经验》(Specifying: Black Women Writing the American Experience,1987),梅·格温多林·亨德森(Mae Gwendolyn Henderson)的论文“用多种语言说话:对话体、辩证法与黑人女作家的文学传统”(Speaking in Tongues:Dialogic and Dialectics and the Black Women Writer's Literary Tradition,1989),以及芭芭·拉希尔·里格尼(Barbara Hill Rigney)的《托尼·莫里森的多重声音》(The Voices of Toni Morrison,1991)等。
进入90年代后期至今,学术界对莫里森的创作和定位逐渐统一,且研究日趋深入和多样。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突出的方面:一是从种族、历史等社会学领域对莫里森的创作进行研究。随着莫里森持续地创作和影响力的扩大,学界逐渐认识到她的创作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黑人女作家”的写作范畴,进而把她置于美国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较多关注到英美文化与非裔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学表征与政治、种族之间的关联。在《危险的自由:托尼·莫里森小说的融合与分裂》(Dangerous Freedom: Fusion and Fragmentation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1995)一书中,菲利普·佩奇(Philip Page)把莫里森小说放到美国文化、非裔美国文化中加以审视,认为莫里森忠实地传达出非裔美国人的“双重意识”;吉尔·梅特斯(Jill L.Matus)的《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98),在政治和历史语境中聚焦黑人的集体创伤和历史书写。简·弗曼(Jan Furman)在其著作《托尼·莫里森的小说》(Toni Morrison's Fiction,1999)中,探索了莫里森哲学体系中常见的人物、主题和场景及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影响;格鲁沃尔(Grewal)的《忧伤不绝,抗争不止》,认为莫里森在作品中重新审视个体和社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确立作品的疗伤和政治功能(2000)。杜瓦尔(John N.Duvall)在《托尼·莫里森的标志性小说:现代主义的真实性和后现代的黑人性》(The Identifying Fictions of Toni Morrison: Modernist Authenticity and Postmodern Blackness,2000)中关注的依旧是莫里森的历史书写,认为她的作品不属于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姆巴利亚(Doreatha Drummond Mbalia)在《托尼·莫里森递进的阶级意识》(Toni Morrison's Developing Class Consciousness,2004)中,认为莫里森的创作展示了非洲后裔如何遭受剥削和压迫,对遭遇的书写表明了作者不断发展的社会意识。费古森(Rebecca Hope Ferguson)的《重塑黑人身份:托尼·莫里森小说的转变和置换》(Rewriting Black Identities: Transition and Exchang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2007),一方面通过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种族理论等,探讨美国黑人身份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突出了莫里森作品的历史和文化变迁主题。
另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注重从文化层面进行批评。凯瑟琳·马科斯(Kathleen Marks)在《托尼·莫里森的 〈宠儿〉和典仪想象》(Toni Morrison's Beloved and the Apotropaic Imagination,2002)中,梳理了从古至今的典仪历史,指出《宠儿》中塞丝的杀婴和萨格斯在林间的集体行为具有典仪特征,黑人的集体创伤在仪式中获得治疗。福尔茨(Lucille P.Fultz)的论著《托尼·莫里森:与差异做游戏》(Toni Morrison:Playing with Difference,2003),将莫里森的系列小说作为精心建构的整体加以审视,揭示了差异间的互动关系——爱与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黑人与白人、过去与现在、富裕和贫穷等;莫里森营造了一个充满意象和文字游戏的差异矩阵,将其他众多差异纳入种族问题中进行宏观考量,显示差异标志对小说人物和叙事进程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展开对决。莫布利(Marilyn Sanders Mobley)的著作《莎拉·奥恩·朱厄特与托尼·莫里森的民俗之根与神话之翼:叙述的文化功能》(Folk Roots and Mythic Wings in Sarah Orne Jewett and Toni Morrison: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Narrative,1991)从文化方面讨论莫里森与其他女作家的关系。
此外,评论界还常常把莫里森和经典白人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大卫·科沃特(David Cowart)比较了莫里森与福克纳和乔伊斯之间的关系;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莫里森继承了伍尔夫与福克纳的传统。斯特拉马里斯·科泽(Stelamaris Coser)的《跨越美洲:托尼·莫里森、葆拉·马歇尔与盖尔·琼斯的文学》(Bridging the Americas: The Literature of Paule Marshall,Toni Morrison,and Gayl Jones,1995)把莫里森的作品置于泛美写作的背景中,特别强调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对莫里森的影响。
国内对莫里森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时的研究大部分都是概述性的介绍。从90年代开始,理论界关注到美国黑人文化、文学批评,程锡麟、王晓路和嵇敏等学者对其研究成果、特征作了介绍和述评。例如,翁乐虹对莫里森的《宠儿》和《爵士乐》的叙述策略做了研究。此外,一些研究者进行了有意义的比较研究,如田详斌的《南美洲交相辉映的两朵艺术奇葩——论 〈所罗门之歌〉和〈百年孤独〉的成功与魅力》;亦有学者把莫里森放在非裔文学的背景中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对象的选择反映了研究者进行比较研究时关注范围的独特性,即对第三世界文学共同命运的关注和对少数群体文学特征及其差异的敏感。这阶段对莫里森创作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研究的是王守仁、吴新云著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1999)一书,该论著把莫里森的创作放在了黑人文学传统中,关注其性别、种族和黑人文化,并结合文本进行分析,使得国内对莫里森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系统。
步入21世纪后,伴随作家持续地创作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对莫里森的研究日趋全面和深入。代表性著作有:2004年出版的朱荣杰的《伤痛与弥合:托妮·莫里森小说母爱主题的文化研究》、胡笑瑛的《不能忘记的故事》。2005年有王玉括的《莫里森研究》,该书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方法,把莫里森置于美国文学传统中考察其文化立场,引入身体政治、戏仿、虚构等术语对文本进行分析,阐明了莫里森对白人文学传统的解构并重新书写了非裔美国人的形象、历史和文化。2006年有唐红梅的《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章汝雯的《托妮·莫里森研究》、毛信德的《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和王泉的《拉康式解读莫里森的三部小说》。2008年有焦小婷的《多元的梦想——“百衲被”审美与托尼·莫里森的艺术诉求》、蒋欣欣的《托尼·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研究》、赵莉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2009年有田亚曼的《母爱与成长》。2010年出版的相关著作包括曾梅的《托尼·莫里森作品的文化定位》、王烺烺的《托妮·莫里森 〈宠儿〉、〈爵士乐〉、〈天堂〉 三部曲中的身份构建》、朱晓琳的《回归与超越——托尼·莫里森小说的喻指性研究》、王玉的《在差异的世界中重构黑人文化身份》、李美芹的《用文字谱写乐章:论黑人音乐对莫里森小说的影响》。曾梅的论著从后殖民背景下的文化批评理论来分析莫里森作品的文化定位,把研究焦点从文学和种族问题转向文学外部研究,探讨了非洲黑人文化、美国黑人文化和欧洲文学,突出了莫里森文学创作的多重文化内涵。论著中非洲传统文化对莫里森的影响部分最为突出。朱晓琳的著作借美国黑人文艺批评家亨利·路易·盖茨(Herry Louis Gates)的喻指理论对莫里森的小说的语言、意象喻指进行了分析,并把莫里森的创作置于非裔和欧洲文学传统中讨论其改写性、继承性喻指。2011年出版的赵莉华的《空间政治:托尼·莫里森小说研究》探讨了种族“空间表征”的构想性以及“空间表征”下黑人的“表征空间”和“空间实践”。2012年有胡妮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田亚曼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域下的莫里森小说研究》和孙艳芳的《莫里森小说的修辞艺术》。2014年有荆兴梅的《托妮·莫里森作品的后现代历史书写》,该论著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对莫里森的小说进行了充分的解读,认为其创作是对官方的宏大叙事的颠覆和重写,彰显了少数族裔的话语权和内心诉求并以此获取文化身份和社会认同。2015年有赵宏维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和修树新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的文学学伦理学批评》。2016年有熊礼伟的《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与伦理批评》。2018年有吴胜利的《托尼·莫里森小说导读》、毛艳华的《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母性研究》。2019年有马粉英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2020年有龚玲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的悲剧意识研究》和马艳的《性别视域下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的身体研究》两部。
除了国内作者研究的著作,我国还原版引进、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史密斯(Valerie Smith)主编的《〈所罗门之歌〉 新论》,罗伯特·W.汉柏林、克里斯托弗·瑞格主编(康毅、王丽丽等译)的《从福克纳到莫里森》等。前者收录了包括从口头记忆、声音和对话结构、名字、政治身份和方言等层面对《所罗门之歌》的研究文章;后者收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学者就福克纳和莫里森作品分析和比较研究的论文。他们运用后殖民理论,从美学视角、文化视角就种族、性别、社会经济以及叙述策略等方面展开对两位作家的互文性研究。
2.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地理相关研究述评
近年来还有大量的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论文共同促进了莫里森研究热,如张宏薇的《托尼·莫里森宗教思想研究》、陆泉枝的《托尼·莫里森的叙事艺术与政治》等。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托尼·莫里森都是一个研究热点,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版和发表,本书无法一一列举。在此基础上,笔者发现莫里森小说中的地理空间现象异常突出而关注者相对较少,本书就此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概括,试图从文学地理空间视角推进莫里森研究。
莫里森作品中的“南方”或者相关南方地理空间问题,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卡罗琳·琼斯(Carolyn M.Jones)的《托尼·莫里森小说中作为精神空间的南方景观》一文认为,美国黑人形成了美国南方景观。美国南方景观,一开始在法律上和经济上与非洲奴隶都是不相容的,但后来在精神层面上逐渐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尽管身处那片大陆,但南方的黑人们并没有真正的归属感。莫里森的小说正是通过景观隐喻表现了这种亲近与疏离。在她的创作实践中,通过记忆和想象力重新强调了这种景观。莫里森在《宠儿》和《所罗门之歌》中揭示了南方如何既作为断裂之处,又作为自我重新统一之处发挥作用。[18]凯瑟琳·凯尔·李(Catherine Carr Lee)的研究文章《〈所罗门之歌〉 中的南方:成长、治疗和家园》讨论了南方地理空间与奶娃自我身份及文化记忆问题。在文章中,作者认为莫里森在小说中颠覆了西方成长小说的模式,进而揭示出拭去了南方记忆的极端个人主义导致了精神毁灭和道德身份丧失。[19]
格罗瑞亚·格兰特·罗宾逊(Gloria Grant Roberson)的《托尼·莫里森的世界:小说中的人物和地方指南》提供了关于莫里森前七部小说的人物和场景索引,没有具体分析,相当于一部研究指南或工具书。[20]英国华威大学泰莎·凯特·罗伊侬(Tessa Kate Roynon)的博士论文《转型美国:托尼·莫里森和古典传统》通过对莫里森的前八部小说的分析,探究了其创作和希腊罗马经典的关系,认为莫里森对古希腊罗马的崇拜是她政治投射的基础。论文的第二部分写到了“南方、奴隶制、内战和重建”涉及了对南方的阐释。她认为,莫里森作品的多重回声逐渐形成了她对殖民、新国家建立、奴隶制及其后果以及民权运动重建中的主导文化立场和文学表征。[21]克里斯托弗·沃尔什(Christopher J.Walsh)在他的文章《“黑色遗产”:南方文学中的哥特式破裂》中指出,哥特风格在美国南方文学中存在断裂,而作为“黑色遗产”的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族、历史等因素成为哥特在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内容。其中谈到了莫里森的《宠儿》,认为这部作品对南方哥特传统有显著贡献,并对哥特的当代化很重要。[22]
法国学者恩东戈·奥马尔在他的文章《莫里森和她早期作品:寻找非洲》中认为,莫里森和福克纳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两位作家,他援引莫里森的访谈录提出其文章的主要观点:莫里森是以“南方”为主要地理空间进行书写的。论文提炼了莫里森早期作品中的一些主题和文学手法来追踪或者强调其对非洲大陆的展现。文章认为,“莫里森在访谈中提到的‘村庄’可以认为是非洲的代表;同时可以理解为那片大陆和神话起源在南方及它在奴隶制中的象征性再现”[23]。201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赫尔曼·比弗斯(Herman Beavers)出版了一部研究著《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地理与政治想象》,该书是近年来较为重要的莫里森研究著作。作者同样关注了莫里森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分别从“北方”和“南方”两部分研究地理空间与政治想象之间的关系。[24]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莫里森作品中突出的南方地理空间现象。曾竹青在其论文《〈所罗门之歌〉 中的记忆场所》中谈到,南方和布鲁斯是《所罗门之歌》的记忆场所。在作品中,莫里森将南方梦幻化和神圣化,为美国黑人打造了一个祭奠黑人集体记忆的殿堂和安抚黑人心灵的精神庇护所。[25]王玉括的文章《非裔美国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及其文化表征》中认为,地理空间在非裔美国文学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作者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文本包括《所罗门之歌》在内,分析了美国黑人从追求自由到追寻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中地理空间的隐喻作用和文化表征。通过对这些地理空间的认同、反思和反讽,非裔美国人不断地追求真正的自由和自我。[26]
还有一部分学者倾向于把莫里森的小说看作是南方文学的代表,并把其与美国南方文学作家和传统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曾利红、黎明在《南方哥特小说中的幽灵意象——兼评 〈押沙龙,押沙龙!〉和〈宠儿〉》中认为,《押沙龙,押沙龙!》和《宠儿》是美国南方小说的重要作品。两部作品都具有哥特小说的幽灵意象,而这些意象深刻反映了美国南方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特性。[27]高卫红、张旭华在《解析 〈宠儿〉及其南方文学特征》中强调了莫里森文学作品中的南方文学特征,即南方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情节、家庭主题和哥特传统。[28]王秀梅在《历史记忆与现实世界的冲突——威廉·福克纳与托妮·莫里森的对比研究》一文中认为,两位作家在对南方历史表达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福克纳的创作表现了美国20世纪南方的现实,而莫里森代表了黑人和女性声音,展现了南方文学的不同侧面。[29]
3.研究意义阐述
第一,将作家晚期创作囊括在内,研究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地理空间和政治想象之间的关系,对理解作家的完整创作轨迹、思想发展历程及其文化立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大部分国内评论主要集中在作品的主题方面,比如莫里森对南方奴隶制的书写。她在文学作品中试图展示黑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情感,把读者带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但作品对南方的书写不仅仅是在展示历史,更表明了作家对这个地理空间赋予的价值,同时呈现出其鲜明的文化立场。另外,很多研究认为莫里森在艺术方面承袭了以福克纳为代表的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特式风格、家族生活、孤独意识的描述等。不可否认,莫里森对南方的书写确实与美国南方文学在美学风格上有一定的近似之处,但其创作又有着迥异之处。作家也曾经表达这样的观点:“我不是乔伊斯、福克纳……”为什么莫里森如此推崇这些作家却又有意拉开距离?仅仅是因为不想被打上“后继者”[30]的标签?为什么她作品中的鲜明特色令人着迷但却不被很多人认可?所以,仅仅从主题和艺术风格方面对莫里森的创作进行研究,在力度和深度方面显然是不够的,不足以展现莫里森的整体创作风貌及其在整个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和意义。
其次,在众多代表性研究成果推出之后,莫里森仍以每三到五年一部小说的频率持续写作,包括各类演讲、访谈等。进入21世纪,作家又出版了几部重要小说,包括2003年的《爱》、2008年的《恩惠》、2012年的《家》和2015年的《孩子的愤怒》。其中,《恩惠》和《家》可以说是其晚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两部,前者在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就职期间出版,叙事回溯至美洲被殖民时期,历史地呈现了美国种族主义产生之前的种族景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少数族裔的民族自信。2012年《家》的出版则揭示出莫里森文学叙事的某种回归,与《所罗门之歌》形成了呼应关系。此外,还有一部重要的演讲集《他者的起源》在2017年出版。这部集子涵盖了《成为陌生人》《色彩崇拜》《塑造他者》《外来者的家园》等文章,作品集中阐述了作家晚年对美国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其创作和个人立场的阐述等。就已有的研究来看,大部分整体性研究没有涉及近几年的作品,也就无法获得作家创作的完整思想轨迹。实际上,早期的“南归”再一次呈现在叙事中,同时带上了浓重的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意味。所以,后期作品对理解作家整个创作历程和叙事逻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第二,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地理空间叙事充分而立体地展示了非裔美国人四百年来在美洲的生活画卷,包括个体体验、民族历史、政治理想等,有效地丰富和修正了白人文学中对“南方”的呈现。早期相关文学创作都是白人移民以“外来者”的眼光来写美国南部生活的,包括时任弗吉尼亚詹姆斯敦的首领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所写的《弗吉尼亚通史》、奥古斯都·鲍德温·朗斯特里特(Augustus Baldwin Longstreet)的《佐治亚即景》等。19世纪出现了两位闻名世界的作家,一位是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另一位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爱伦·坡的《厄舍屋的倒塌》《怪异故事集》等作品以哥特式风格,癫狂、阴郁、奇特的想象在其文学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暴力和恐怖的世界,确立了南方文学的审美走向之一。爱伦·坡在其作品中也表现出对“纯洁”种族观的质疑和颠覆。[31]马克·吐温的小说以南部小城镇、乡村作为其故事背景,对狩猎、男女间的爱情婚姻、葬礼、家庭聚会等日常琐事进行描写。同时,他还以孩子的视角描写美国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
内战后的“新南方”作家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南方和整个美国的未来。在这新一代作家当中,乔治·华盛顿·凯布尔(George Washington Cable)和乔埃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ris)成就最为突出。凯布尔是较早意识到黑人问题严重性的作家,他的《寂寞的南方》和《黑人问题》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的两部严肃题材的小说作品。哈里斯塑造的“莱姆斯大叔”(Uncle Remus)是美国文学中三位最“显赫”的黑人形象之一。南方文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了大规模的复兴,产生了一大批作家、诗人、戏剧家、学者、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福克纳,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文学系列呈现出的“南方”是由个人史、习俗、信仰、神话、幻想等构成的复杂世界,秩序残破,人物孤独、扭曲、挣扎,充满悲情色彩。
美国文学中关于南方的叙事,大部分是基于白人生活的,极少把黑人群体作为叙事中心进行书写,即使作品中有黑人出现或者种族冲突,人物或者被类型化,要么事件本身也无足轻重,都是以背景被嵌入白人的生活中。南方作家们创造了一系列“神话”:奴隶主普遍都被美化成善良而仁慈的人,他们尽力照看自己的黑奴,而奴隶们则对主人忠心耿耿并为之辛勤劳作,比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尽管评论没有确指这是一部南方小说,但其涉及的问题却离不开南方的背景)中的汤姆。与“神话”相对的是一类丑恶黑人形象,如野兽、荡妇、小丑之流。此外,尽管有一部分作家意识到了种族问题,但始终是以一种“他者”的姿态看待种族问题和黑人生活,提供了一个经过白人眼光“过滤”和想象的黑人生活画卷,比如爱伦·坡、福克纳等作家。在莫里森建构的“南方”世界里,黑人群体始终是叙事的中心,作家也是以“人民”的身份对其进行观察和书写的。故此,莫里森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白人文学中对南方的呈现,修正了“他者”眼光中的“南方”,展现了作为主体的黑人眼中的“南方”及其生活画卷。
第三,莫里森关于南方地理空间的叙事揭示了作家对美国当代黑人困境的深入思考并试图提供某种解决路径。早期非裔美国文学有两个基本主题:对基督教博爱精神的深信不疑和对自由平等的现实追求。被视为美国国家文学和非裔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生平叙事》叙述了以美国南方为背景的个人生活经历,道格拉斯最终成功逃到北方,摆脱了残酷的奴隶制对人的压迫。它奠定了非裔美国文学中地理书写的基本方向:“南方”是深重苦难的现实之地,而“北方”成了自由的代名词,逃亡北方成了一种希望。
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开创了非裔美国文学的新纪元,此时非裔美国作家才真正具有自我意识,代表作家主要有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琼·图默(Jean Toomer)、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康蒂·卡伦(Countee Cullen)、阿莱恩·洛克(Alain Locke)、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s)等。到了40年代,以理查德·赖特(Richard White)为代表的非裔作家开始在作品中集中反映各种社会问题,如大迁移、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等,同时突出了种族抗议,非裔美国文学逐渐走向成熟。1940年,赖特的小说《土生子》的出版轰动了美国文坛。该书描述了非裔美国人的恐惧、仇恨和暴力及其被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扭曲的心灵,同时揭示了“坏黑人”被充斥着种族主义的社会“制造”出来的过程。
二战以后,非裔美国文学蓬勃发展。虽然非裔美国人摆脱奴隶制已经一个多世纪,但种族压迫和种族隔离依旧存在。这时的非裔美国作家主要展现他们在美国艰难的生存环境,抨击种族偏见和社会不公。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小说《向苍天呼吁》描写了黑人青年的生活经历,探索美国黑人的身份危机。拉尔夫·沃尔多·埃里森(Ralph Waldo Ellison)的《看不见的人》揭示了非裔美国人在充满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社会氛围里追求自我的悲哀和无奈。民权运动时期,非裔美国文学的思想特征是要求做人的尊严,获得平等民权,倡导黑人民族主义、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80年代以来,非裔美国文学描写的重点是黑人社区经历并致力于阐释黑人身份的意义。这个时期的文学不是倡导以牺牲黑人文化为代价的种族融入,而是提倡他们以非裔美国人身份进入美国社会,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推动美国多元化的民主进程,托尼·莫里森、爱丽丝·沃克、玛雅·安吉娄等作家成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
莫里森的十一部小说清晰地呈现了她的创作轨迹,从个人成长到社会理想以及宗教观念,无不透露出作者的鲜明文化立场。莫里森继承了非裔美国文学中突出的地理空间书写传统,并将这种书写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政治内涵,将这种书写当代化。约翰·伦纳德评价《爵士乐》时指出,读莫里森的作品发现,她迟早要去南方。[32]正是通过对想象中的“南方”地理空间的遥望和书写,作家表达出鲜明的文化立场并号召自己的人民坚守民族文化。回归南方就意味着回归民族,回归群体,南方被塑造为非裔美国人的精神家园。莫里森曾说,“有成千上万的像梅德林一样的小城,那儿是大部分黑人的聚集地,是黑人的精神源泉,就是在那儿我们构建了自己的身份”[33]。
美国学者格里森将“‘南方’看作一种‘文化建构’,认为‘南方’是美国的‘内部他者’——尽管是民族身躯的‘固有组成部分’,却‘被割裂于整体之外,遭受另眼相待’;于是,‘我们的南方’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构成了一种‘既结盟又背离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文化政治学的视野中又被进一步表明,对于现代民族而言,那些在物质意义上身陷边缘的因素恰恰在象征意义上成为了中心元素”[34]。美国“南方”就是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它成了一种象征。在这个地理空间中,当代非裔美国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疗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带来的情感伤害,也可以缓释源自现代资本社会和消费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和困扰,最终与社会达成和解并安放现代人漂泊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