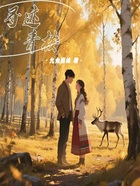
第4章 独龙江·纹面与绳结
2010年冬·怒江独龙江流域
独龙江的雾是活的。
它从碧罗雪山与高黎贡山交错的褶皱间涌出,裹挟着冰碛石的寒气,将藤网桥浸成了墨绿色。
结束了最后一个学期的交流,我马不停蹄地回国。回到五年前分别的地方,天笑却不知所踪,只有我抓拍他在岩壁舞蹈的那张模糊照片。
这次轮到我去找寻他的踪迹了……
第一站就是怒江峡谷。
我攥紧背包带,看着前方引路的纹面女阿南婆婆——她佝偻的脊背像一张拉满的弓,脸上的靛青纹路如藤蔓缠绕,那是独龙族最后的活态史书。
(1)藤桥上的蝴蝶结与婆婆的纹面刀
“抓紧!这桥吃人!”阿南婆婆用独龙语警示。
藤网桥在江风里摇晃,三十米下的江水翻腾出白沫。我学着婆婆的姿势横移,指尖触到藤条上凸起的绳结——竟是改良过的“蝴蝶振翅结”,绳芯缠着防水尼龙线。
“这结法……是外面人教的?”我问同行的普纳。
“去年有个登山队来训练,”他指向对岸崖壁,“李哥刚好在这边,和他们交流来着。李哥说这叫‘文明的锚点’。”
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是天笑。岩壁上残留着几枚岩钉,钉孔周围的青苔被镁粉染成灰白——像极了漓江月亮山的岩点布局。
阿南婆婆的火塘终年不熄。她握纹面刀的手稳如磐石,刀刃在松明火中淬炼:“我十三岁纹面那天,江上漂来解放军的第一袋盐巴……”我按下录音键,磁带沙沙转动,老人的叙述与江涛声交融。
深夜整理素材时,我鬼使神差地想要将独龙族古调与漓江录音拼接。天笑教绳结的笑声撞上阿南婆婆的纹面歌谣,竟在微型卡式机里酿出奇异的和声。
(2)雪封孤村的荞麦粑粑与漆油鸡里的银铃铛
到怒江的第五天,就突降暴雪,百年不遇的大雪引起了雪崩,今天已经是封山第十日了,盐巴即将告罄。我缩在漏风的木楞房里誊绘纹面图谱,忽然听见马铃声撕开雪幕——普纳扛着巨大的补给袋跌进门,袋上印着“云南登山协会”的徽标。
“登山协会的人和附近的驻军战士凿通了雪崩区!”他甩出袋冻硬的荞麦粑粑,“这是他们送来的补给。”
登山协会会不会有他的消息,我拿出笔记本中的那张泛黄老照片思索——多年前漓江畔,我拍糊的那张废片被天笑几年前用显影液强行洗出。天笑的侧影浸在光斑里,背后写着:“有些画面,时间会显影。”
又是半个多月过去,依旧没有天笑的消息,不过卡雀哇节将至,阿南婆婆邀我与她一起度过这个庆典。
节日前夜,全寨都在烹制漆油鸡。金黄鸡块在漆树籽油里翻滚,阿南婆婆突然往锅里扔了枚银铃铛:“吃到这个的话,山神就认你是独龙的姑娘啦。”
咬到铃铛时,我的舌尖泛起似曾相识的凉意——和鄂温克祖母给我护身符时一模一样。普纳醉醺醺地大笑:“李哥最近几年经常来我们这里,他也吃过这个!他还说要带个鹿铃姑娘进山……”
篝火映红了我的耳尖,我小心地将铃铛穿进银丝发带,就像是山神给予我们的共同信物一般。
开春出山那日,藤网桥多了串绳结,绳结的末端系着一小块印着Halfway的压缩饼干——那是当年何老板专门定制了送给他客栈友人的特供粮。
“这是李队留他心上人的暗号吧!”普纳兴奋地比划着,将解下的绳结交给我。
江风卷走未尽之言,独龙江的雾又漫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