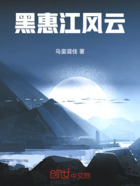
第37章 笫38章 热血青春
一、出征
一九七〇年三月,黑惠江边彝山还带着冬末的寒意。段洋站在自家土屋前,望着远处起伏的群山,手里紧攥着那封通知书。
“洋儿,真要走了?“母亲撩起围裙擦着手,从灶屋走出来,眼里满是不舍。
段洋转过身,看见母亲花白的头发和粗糙的双手。
“阿妈,这是光荣任务。“段洋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美国人在老挝扔炸弹,我们的同志需要路运送物资。“
母亲没说话,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拿着,庙里求的平安符。“
段洋接过还带着母亲体温的布包,喉咙发紧。布包里是一枚铜钱,用红绳系着,简单却沉重。
三天后,段洋背着简单的行囊,和全公社选拔的三十多名人员一起,踏上征程,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晨雾中。
抵达昆明后,队伍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集训。主要学习老挝的基本情况、安全防护和简单的老挝语。段洋学得认真,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你好“、“谢谢“、“小心炸弹“之类的词汇。
“听说那边蚊子比苍蝇还大,一咬一个包,能让人发高烧。“同屋的小张晚上躺在床上嘀咕,“还有蚂蟥,能从鞋缝钻进去吸血。“
段洋没接话,只是翻了个身。他从小在山里长大,不怕虫子,但听说美军经常轰炸筑路队,这让他心里发紧。
四月初的一个清晨,队伍终于要出发了。所有人换上统一的蓝色工装,背着打包好的工具和行李,登上了解放牌卡车。
车队沿着颠簸的土路向边境驶去。越往南,植被越茂密,空气也越发湿热。段洋的工装后背已经湿透,贴在身上很不舒服。
“前面就是磨憨口岸了!“领队老王站在车头喊道,“大家检查一下证件!“
段洋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护照和介绍信,心跳加速。边境检查站很简陋,一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磨憨口岸“的木牌,几间平房,还有持枪站岗的士兵。
过关手续比想象中简单。核对名单、检查行李后,车队缓缓驶过界碑。段洋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祖国,然后转向眼前陌生的土地——老挝,他即将奋斗的地方。
二、原始森林
进入老挝境内,道路立刻变得崎岖难行。卡车在泥泞的土路上颠簸,有时不得不停下来,等工兵在前面清理路障或填平弹坑。
“这些都是美国佬炸的,“老王指着路边一个直径近十米的弹坑说,“他们专门炸路,想切断我们的运输线。“
段洋看着那个深坑,想象炸弹落下时的场景,手心冒汗。车队又行驶了几个小时,天色渐暗时,他们终于抵达了第一个营地——位于老挝北部原始森林边缘的一处临时驻地。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未来几个月要住的地方!“老王跳下车,指着几排竹棚,“男同志住这边,女同志住那边,食堂在后面。明天开始分组,先修通到主工地的支线。“
营地简陋但整齐。竹棚搭在离地一尺高的木架上,以防雨季洪水。每间棚子里摆着十几张竹床,蚊帐整齐地挂在上面。
段洋放下行李,刚想躺下休息,突然听到一阵骚动。
“蛇!有蛇!“有人惊呼。
一条近两米长的绿色大蛇正从竹棚的横梁上滑下来。段洋从小在山里长大,一眼认出这是条无毒的青蛇,但体型之大还是让他吃了一惊。
“别动!“他抄起门边的竹竿,轻轻挑住蛇身,迅速走到门外将蛇放生到远处的草丛里。
“小段,身手不错啊!“老王拍拍他的肩膀,“以后你就是咱们棚子的'除蛇专员'了。“
当晚,段洋在油灯下写下了第一封家书,告诉母亲他已安全抵达,一切都好。他没提蛇,也没提路上看到的弹坑,更没提营地周围不时传来的飞机轰鸣声。
第二天天刚亮,刺耳的哨声就把所有人叫醒。早餐是稀粥、咸菜和馒头,然后立即开始分组。段洋被分到了勘测组,负责公路线路的测量和标记。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勘测从营地到主工地的五公里支线。“勘测组组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程师,姓李,戴着厚厚的眼镜,“段洋,你负责记录数据。“
原始森林里的勘测工作异常艰苦。茂密的植被遮挡视线,湿热的气候让人喘不过气,各种昆虫更是无孔不入。段洋的脖子上很快被蚊子叮满了包,汗水一浸,又痒又痛。
“小心!别碰那棵树!“当地向导突然用生硬的汉语喊道,“树上有火蚁!“
段洋赶紧缩回正要扶树干的手。向导是个瘦小的老挝青年,叫坎苏,会说一些汉语。他指着树干上几乎看不见的小红蚂蚁:“这个,咬人很痛,会发烧。“
中午休息时,坎苏教大家辨认哪些植物有毒,哪些可以食用,哪些能驱虫。段洋学得认真,还特意记在笔记本上。
“你,好学。“坎苏对段洋竖起大拇指。
下午的勘测更加艰难。有一段路必须穿过沼泽,李工程师的眼镜被汗水模糊,差点跌进泥潭,幸好段洋眼疾手快拉住了他。
“谢谢小段,“老李惊魂未定,“我这把老骨头要是掉进去,可就麻烦了。“
天黑前,勘测组终于完成了当天的任务。回到营地时,段洋的工装已经湿透,手上被荆棘划了好几道口子,脚底也磨出了水泡。但看到记录本上完整的数据,他心里涌起一股成就感。
晚饭后,营地组织了一场简单的欢迎会。来自不同省份的技术员们表演节目,有唱样板戏的,有说快板的,气氛热烈。轮到云南组的同志时,他们表演了一段彝族舞蹈,领舞的是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叫阿木呷。
“我是凉山彝族的,“表演结束后,阿木呷坐到段洋身边,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语说,“我们那里,山比这里还高。“
段洋把彝族阿木呷当做自家人,两人聊到熄灯号响起。
三、轰炸
一个月后,支线公路修通了。段洋已经适应了老挝的气候和工作节奏。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手上的茧子厚了一层,还学会了简单的老挝语。
“阿木呷,'吃饭'凉山彝语怎么说?“休息时,段洋问。
“咋啦,你想去我们凉山找媳妇?“阿木呷打趣道,然后认真地教他,“'吃饭'说'措礼'。″
段洋记在笔记本上,旁边还画了个小人端碗吃饭的简笔画。他从小喜欢画画,虽然没有专门学过,但能抓住特征。笔记本的空白处渐渐填满了各种速写——营地、工友、老挝的山水。
主线路的工程比支线艰难十倍。要穿过密林,跨越溪流,有时还要爆破山石。美国飞机的骚扰也越来越频繁,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爆炸声。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分成昼夜两班倒!“一天早晨,老王严肃地宣布,“白天主要做准备工作,夜间施工,减少被轰炸的风险。“
段洋被分到了夜班组。夜间施工有特殊的困难——照明不足,视线受限,还要提防野兽和毒虫。但至少,美国飞机晚上很少出现。
五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段洋正和组员们在一段陡坡上架设支撑架。突然,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声。
“飞机!隐蔽!“哨兵大喊。
所有人立刻熄灭灯火,迅速躲进预先挖好的防空洞。段洋和阿木呷挤在一个狭小的洞内,能清晰地听到飞机由远及近的呼啸声。
“别怕,他们晚上看不清目标。“阿木呷低声说,但段洋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飞机在头顶盘旋了几圈,投下几颗照明弹。刺眼的白光透过防空洞的缝隙照进来,段洋屏住呼吸,心脏狂跳。几分钟后,飞机声渐渐远去,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狗日的美国佬,“爬出防空洞后,一个老工人骂道,“有本事白天来,看老子不用步枪把你打下来!“
段洋没说话,只是默默检查工具和设备。照明弹没有造成直接破坏,但耽误了两个小时的工作进度。
第二天晚上,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这次飞机飞得更低,甚至能看清机身上的标志。照明弹把整段工地照得如同白昼,紧接着是一连串的机枪扫射。
“所有人别动!别出声!“老王的声音从另一个防空洞传来。
子弹打在岩石和树木上,发出可怕的声响。段洋紧紧贴着洞壁,手里攥着母亲给的平安符。突然,一声巨响,大地震动,尘土从防空洞顶簌簌落下。
“炸弹!“有人惊呼。
等飞机离开后,大家爬出来查看损失。一颗炸弹落在了刚修好的路基上,炸出一个大坑,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今晚收工,“老王脸色阴沉,“明天白天再修。“
回营地的路上,段洋发现阿木呷走路一瘸一拐。
“怎么了?“他问。
“没事,可能扭到脚了。“阿木呷勉强笑了笑。
但第二天早上,阿木呷没来吃早饭。段洋去竹棚找他,发现他发着高烧,右脚肿得像馒头。
“昨晚被弹片擦到了,“阿木呷虚弱地说,“不想让大家担心,就没说。“
军医检查后,发现伤口已经感染,必须立即处理。段洋主动请缨照顾阿木呷,每天给他送饭换药。
“段哥,你人真好,“一天晚上,阿木呷感激地说,“等打完仗,你一定要来我们凉山玩,我让我妹妹给你做苦荞饼。“
段洋笑着答应,心里却想,等打完仗,谁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四、伤痕
六月底,工程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必须在一处悬崖边开凿路基。这里地势险要,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是几十米深的悬崖,作业面狭窄,机械施展不开,大部分工作要靠人力完成。
更危险的是,这段路正好在一个战略要地附近,美军飞机几乎每天都会来轰炸。为了赶进度,工程队不得不冒险在白天施工,只是加派了更多的瞭望哨。
“同志们,这段路必须在一周内打通!“动员会上,老王的声音嘶哑,“前线急需物资,我们没有退路!“
段洋被分到了爆破组,负责打炮眼、装炸药。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需要精准计算药量,既要炸开岩石,又不能破坏整体结构。
七月三日,一个闷热的上午,段洋正和两名工友在崖壁上打炮眼。突然,瞭望哨的哨声尖锐地响起。
“飞机!东北方向!隐蔽!“
所有人立刻放下工具,向预先挖好的掩体跑去。段洋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阿木呷还在崖壁上方收拾测量仪器。
“阿木呷!快下来!“他大喊。
阿木呷似乎没听见,仍在专注地收拾设备。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段洋顾不上多想,转身往回跑。
“小段!你干什么!回来!“老王在身后怒吼。
段洋充耳不闻,几步冲到崖壁下:“阿木呷!飞机来了!“
阿木呷这才抬头,惊恐地发现飞机已经近在咫尺。他慌忙往下爬,但慌乱中一脚踩空,仪器箱从手中脱落,重重砸在下面的岩石上。
段洋冲上前想接应他,就在这时,第一颗炸弹落了下来。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段洋感到一股热浪袭来,接着是尖锐的疼痛。他下意识扑向阿木呷,两人一起滚进旁边的岩缝中。更多的炸弹落下,大地剧烈震动,碎石和尘土四处飞溅。
不知过了多久,轰炸停止了。段洋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右手鲜血淋漓,一块弹片深深嵌在手背上。阿木呷在他身边,满脸是血,但看起来伤得不重。
“段哥!你的手!“阿木呷惊呼。
段洋想说话,却感到一阵眩晕。再次醒来时,他已经躺在营地的医务室里,右手缠着厚厚的绷带。
“弹片取出来了,没伤到骨头,但会留疤。“军医说,“你很幸运,再偏一点,这只手就废了。“
阿木呷站在床边,眼里含着泪水:“段哥,谢谢你...要不是你...“
“别说这些,“段洋勉强笑了笑,“我们是同志,是兄弟。“
因为手伤,段洋被暂时调离爆破组,改做相对轻松的物资管理工作。这让他有时间整理之前的笔记和素描。他画下了被炸毁的路基,画下了受伤的右手,也画下了阿木呷照顾他的样子。
阿木呷则每天都来看他,教他更多的彝语,还给他唱彝族民歌。段洋发现彝语和老挝语有些发音相似,学起来很快。
“等路修好了,我一定要去你们凉山看看。“一天晚上,段洋对阿木呷说。
“一定来!“阿木呷兴奋地说,“我家的苦荞酒,管够!“
五、归途
十月底,经过七个月的艰苦奋战,公路终于全线贯通。竣工典礼上,老挝方面的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中国同志的国际主义援助。
“这条公路,将永远见证中老两国人民的友谊!“翻译将老挝代表的话转述给大家。
段洋站在人群中,右手上的伤疤已经愈合,但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痕迹。他看着眼前蜿蜒伸向远方的公路,想起这半年多来的点点滴滴——蚊虫叮咬、炸弹威胁、阿木呷的歌声、坎苏教他认的草药...这一切都将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同志们,我们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老王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回国了!“
欢呼声中,段洋看到阿木呷在偷偷抹眼泪。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回国后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当晚,营地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老挝村民送来了自酿的米酒和新鲜水果,大家唱歌跳舞,直到深夜。段洋和阿木呷坐在角落,共饮一壶酒。
“段哥,这个给你。“阿木呷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木雕,是一只展翅的雄鹰,“我们彝族的吉祥物,保佑你平安。“
段洋接过木雕,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翻遍行李,最后把那本画满素描的笔记本送给了阿木呷。
“这里面有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段洋说,“你留着,别忘了我。“
第二天清晨,车队缓缓驶离营地。段洋从车窗望出去,看到坎苏和阿木呷站在路边挥手,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尘土中。
回国后,段洋被分配到云南边疆的公路建设部门。他没有回贵州老家,而是选择继续在边疆工作。援老经历让他成长了许多,也让他对边疆少数民族有了特殊的感情。
每当夜深人静,他都会看着右手上的疤痕,想起老挝的原始森林,想起阿木呷教他的彝语,想起那些在炸弹威胁下并肩作战的日子。这些记忆,就像母亲给他的那枚铜钱一样,被他珍藏在心底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