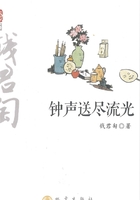
第13章 我和书法的因缘
我不是书家,虽然写了七十多年字,只是一个书而无法的老学生。当我试图叙述那些记忆中的吉光片羽时,它们又被时间的劲风吹散了。我原名玉棠,生于浙江省桐乡县屠甸镇,七岁进入国民学校初等小学。当时修业时间四年,才能升入高等小学,再念三年可以毕业。这种学制是民国初年开始的。
我七岁开始“描红”,描红簿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二开本书籍那么大,每面两行,每行四字,字体近于馆阁,光滑呆滞,纤秀骨弱,也是清末科举制度的余风。我描红的速度是全班第一,老师时加夸赞。由于孩子的自重和虚荣心的奇妙结合,我只想保持描红冠军的荣誉,在假期也不停地苦练,使我受益不浅。八岁之后学习写印版。用毛边纸或金川连订成本子,木版刻印的字范放在夹层间,让孩子们隔一层纸影写。这比描红的程度高得多,因为要先有点写字的底子。写印版,我仍然是头一名缴卷,分数比别人要高五分到十分。老师把我的作业交给全班传阅,我心里很高兴。别的小朋友写字,每笔开头的地方和横画收笔的地方,以及横竖转折的地方,都要停下笔来顿几下,这样颇费时间,我只略一停顿就带过去了,运笔比较灵活,从而取得了为同学们所羡慕的速度。因为我写字的线条比较流畅,书画同源,所以图画成绩也名列前茅。小朋友们最关心的是算术、语文,对我书法上的一点成绩,并不妒嫉。
三载韶光,转眼过去。级任老师钱作民先生认为我的成绩出众,不需要再上四年级,可以跳过一年,直升高等小学攻读。当年学籍管理颇严,不许学生跳级。钱老师把我的名字改成“锦堂”,算是瞒上不瞒下,作为新生入学而通过了。
钱老师和丰子恺老师是好友,思想进步,重视孩子们的个性的发展。他说:“你们喜欢临什么帖,可以自由选择,我不强求你们千篇一律,但是一定要用功,把字练好。这样,日后找到工作,人家看不出你的深浅;否则,纵有一肚皮学问,因为字写得差,往往被人轻视,甚至找不到工作。”
我对碑帖的认识十分欠缺,便买了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天天临写,非常起劲。当然只追求形似,谈不上领会前人的妙处。钱老师的多次表扬,听得我心花怒放,孩子的心是极容易满足的。
在前后两排教室之间有一条长廊,上面盖着瓦片,靠天井的一面是一堵矮墙,只有三尺高,上面用一尺见方的青砖铺成,不糊石灰,显得干净利落。每逢寒暑假,我便找一把棕帚,蘸着清水,在每块方砖上面写一个大字,等写到最末一块,先前写的字迹已经被方砖吸收了,我便再从第一块写起。写大字,我没有临帖,只是自由发挥,在运笔和结体上全像柳字。同学中有的买有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有的买了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我都借来反复阅读,但是没有去临它们。我不喜欢馆阁体,对黄自元的《正气歌》《间架结构帖》,陆润痒的《西湖帖》(文为袁中郎所作),只翻了一翻就不想看了,因此没有受到这些书家和书法的影响。
钱老师认真看了方砖上的大字,心情激动地说:“好孩子!你小小年纪写擘窠大字,很好。但是不应当满足,光写大字还不行,还要练蝇头小楷,小楷将来应用的机会更多。”
“小字练哪一家最好呢?”
“学写《灵飞经》吧,这本帖写得秀而有骨,比较难学,就看你的毅力了。”钱老师和蔼可亲地说。
钱老师是一位爱护幼苗的好老师,至今,我对他很感激。在小学教师中,有他那样的学识的十分难得,吃亏的是他对碑学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否则学生的起点会高一些。我不是说今天的小学生要练北碑,但是书法是一种发挥个性的艺术,如果遇到气质禀赋很优异而又勤于临池的孩子,引导他们跨过唐代以后的字,在隶篆方面打好基础,追求质朴壮美之境,成就会高得多。对前人不可苛求,我寄厚望于来者。
由于气质不合,我写《灵飞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没有十分长进。尽管同学们不断夸奖,我仍未丧失自知之明。如果说到收获,倒是在个性的冶炼上,使我变得比较坚忍。小朋友们拿来折扇,要我写字。我一开始不敢写,也不知道该写什么。年龄大的同学说:“写个‘清风徐来’好了。”这几个字笔画少而易于排列,写来并不吃力。但凡有人指定要写《灵飞经》的,总是达不到方正停匀的效果,每次都失败。
1923年,我进了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由于丰子恺老师的提倡,学校对书法很重视。第一学期就接触到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先生)的书法,无论老师和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当时我对唐代以前的书法,所知有限,弘一法师练的是北碑,自然看不出它的妙处。我便向老师提问:“这字好在哪里?”
老师喜欢好问的学生,并不以为我唐突冒失。他带着微笑回答道:“这种字体比你爱写的柳公权早得多;柳字也是从碑中嬗变出来的,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柳公权和颜鲁公对书学贡献很大,都是唐前旧法度的破坏者。他们的笔画多在两头用力,中间平弱,没有北碑遒劲。现在你阅历较浅,对弘一法师的字里面包含着的生活修养还看不到。他的作品不怕远看、近看、整体看、分别看、反复看。达于此境是很难的。”
“学习写北碑,应当从哪里人手呢?”我被先生说得动了心。
“先写《龙门二十品》,也可以从《石门颂》启蒙。随你选择就是了。”
“什么叫《龙门二十品》?”
“洛阳龙门山有北魏以来的大量石窟佛像,叫做《龙门造像》,有些造像刻有文字,记载造像经过。清人选了二十种,其中包括颇有代表性的《始平公》《杨大眼》《魏灵藏》等。用笔雄健朗润,力度很强,变化很多,可以看出魏时书法的面貌,应当多看!”
“哪儿有这些碑帖?”我一向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
“旧书店里多得很,有旧的,也有新的。有些常常放在里面,如不同店员打交道,是买不到好拓本的。”
星期天,我来到福州路踯躅,这里两旁有很多书店,按照老师讲的方法,我边看边问,很快就买到了《龙门二十品》,携回宿舍,真有些喜出望外,马上灯前细看,的确很有趣味。过去,有的同学告诉我:于右任的字写得很好,我却不懂好在何处。看了《龙门二十品》,慢慢地有点认识了,知道书法学到那种火候,是需要功力的。
我选了《始平公》作为范本,天天临写,原因是:这种字体的结构运笔在揩隶之间,较易掌握;第二是这部帖为白底黑字,较其他十九品来得清楚,开始临习,笔笔露锋,腕力也嫌不足,缺少悬腕的功夫。有位好心的名叫沈世咏的同学对我说:“君匐,你这些方笔都是做出来、描出来的,这样下去字要写坏的。”他教我如何用笔把画划写方,还教我调整笔画,粗细搭配。这样练了一阵子,笔下的方圆就比较随意了。
北碑浑厚庄重,拓墨较少,损坏不多,接近原貌。当时流行的这种字体,原来也不尽是方笔,由于工匠求速度,刻字时用凿直入,把原来的圆笔都刻成了方的。写了一时期,我体会到刀的趣味不是用笔可以求得的,逐渐对篆刻产生了兴趣。学校里的功课除去木炭画、水彩画、油画、图案之外,也讲授国画,由花鸟画家沙辅卿,山水画家杨东山两位教授担任主讲。他们都主张学书法,至于选什么字帖来学,他们并不干预,只强调不要太肥而落入流俗,也不要太瘦而陷入纤巧,允许写得和帖不一样。
每到星期天,我去逛城隍庙。那里旧字画极多,有的放在地摊上,有的挂在店门口,索价低廉。可惜我太穷,只能看,不能买。曾记得当时有一种被称为“帖体”的怪字,结体笔画都和正体不一样。以“豚”字为例,往往写成“默”字。在北碑中这些怪字更多,我也模仿着写,觉得能写这种怪体,可以显示出一己的学问。这自然是可笑的。学校中还有手工课,包括木工、金工、石膏工、篆刻,等等。因为过去很少接触这方面的知识,更没有实践过,所以这时听到别人谈论篆刻,有许多行话听不懂,心中颇有点纳闷,问了人家,无论人家怎么解释,仍是隔靴搔痒。我便买了刀和青田石,刻了磨去,磨了再刻,不得要领。暑假回家,前辈孙增禄和徐菊庵两位先生见到我刻的印,很关心地说:“你这样瞎子摸天窗刻下去,要成为匠人,没有法度和味道。应该先照名家印谱刻几年,再寻自己的路子。现在吴昌硕的印大受欢迎,不妨找他的印谱来摹刻。”
我照着摹刻了几十方印,孙、徐两位先生看了,都皱着眉头说:“吴缶老的味道你刻不出来,只觉得破破烂烂,像一团棉絮。是不是再求远一点,学学赵之谦看。再说,只顾刻而不写篆书,不懂得笔意,进步自然缓慢,可以边写边刻,齐头并进。”
“写什么帖最能提高我的篆刻呢?”
“如果印学昊昌硕一派,那么买一本《石鼓文》来临一临;《石鼓文》与吴昌硕刻印的风格是分不开的。如果印学赵之谦,要写赵之谦一路的篆书。”
“什么叫《石鼓文》?”
“中国古代的石刻文字。目前能见到的以此为最古,是用籀文写的十首四言诗,讲的是秦国国君游猎的情形,唐初在陕西凤翔出土,现存故宫。石鼓文的底子打好了,吴派的印也可以刻好。”
“多少钱一本呢?”
“要银洋两块呢!就怕你母亲不肯给你钱,贵是贵了一些……”
我回到家中,向母亲说要两块银元买一本书。母亲听了说:“什么石鼓?那么贵!”
“好妈妈!我只求您这一次。到上海之后,我一定想办法省下这两块钱来,人家一个月洗澡、剪头发两次,我减少一半,不买零食吃,也不坐电车,找旧的纸头练字。答应吧!”我苦苦纠缠着。
“这孩子想啥个石鼓想煞了,……给你吧,要用心念书啊!”
我接过两块钱,觉得钱上还保存着母亲的体温,捧在手中,仿佛是一团烈火。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想起母亲对儿子无所不包的爱,想到入世谋生后所遇到的冷眼,想到自己迄今学无所成,深负慈望,我的眼眶润湿了。
我把钱寄到上海书店,一周后就收到了一本《石鼓文》。我反复欣赏,夜以继日地边临边读,有时一看半个小时,呆坐不动,犹如老僧人定。
一年以后,菊庵先生看了我的字和印,批评说:“写《石鼓文》有些风骨,可以帮助你摆脱甜俗柔媚的东西,成绩斐然。但是写《石鼓文》刻赵之谦风格的印,二者矛盾、牵制,不如写赵之谦的《汉铙歌三章》,或者直接写汉碑额,这样字与印风格合一,进境就速。”
母亲听到我又要买书,不觉哑然失笑:“去年你不是说过,买《石鼓文》是最后一次要钱吗?”
我只有傻笑,红着脸,低下头去。母亲把钱悄悄塞进我的衣袋,看我一副尴尬相,就走了出去。
不久,我买到了《汉铙歌三章》。从此,学字与学印都宗赵之谦一家,果然面目一变。是年孙增禄先生要我治印两方:“两陂高兴”“孙增禄印”,徐菊庵先生也要我为他刻“徐菊庵印”“殳山外史”等印。这样一来,出了一点小名气,求索者渐多,我也得到了更多的临池与奏刀的机会。写字和刻印这两门相通的艺术互相促进,帮助我渐渐地成长起来。
自从前辈徐菊庵向我推荐赵之谦的《汉铙歌三章》后,我对它着实迷了几年,细想起来,并非坏事。赵之谦治印先工浙、皖两派,后突破秦汉印玺的限制,从汉镜铭、古钱币等吸收营养,开了刻印的新门户,与同时代人相比,很是突出。我对他的作品十分喜爱,虽然后来在书法上跳出了他的门户,但受他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此后,我不再临写弘一法师的字,不过对他的书法至今仍爱好。比如他写“寸”字,写完一竖便将笔收住,不连接着把笔踢起来形成一个钩,而是用一点代之,这种写法古朴有趣。后来我搜求到他的墨迹有十件,其中九件对联、一件朱书立幅《南无阿弥陀佛》,十年浩劫中全部在抄家时被拿走,至今没有还我。
我常读《礼器碑》。此碑写得瘦硬雄浑,气度恢弘。也爱《华山庙碑》,碑的内容无非是祭祀山岳,祈求老天爷及时降雨等,字却写得很有气势。我常常临写这两种碑文,得到的启迪很多。子恺师说过:“读碑帖宜多,以广见闻,临碑帖应侧重一家,以免弄得风格杂沓,非驴非马。”这话很有见地。早年他写魏碑,后来,从魏碑笔法人手写行书,运笔流转,神态飘逸,沉厚而有书卷气。他还告诫我说:“我写字无意作书家,逸宕酣畅的笔势不是刻意求得,而是无意得之。你走拙朴浑涵的路很好,千万别写得和我一样,学古人得形似易,得其神髓却很难。得而能化,更出己意,化古为新,难之又难,非苦干不可。你看弘一法师,做一行像一行,异常认真。出身豪华门第的公子哥儿们,很少肯用功,他却拼命用功,才能在诗、词、书、画、金石、戏剧、音乐各方面都获得卓越的成就。当他扮演《茶花女》一剧的女主角时,活像一个茶花女;当《太平洋报》记者,像一个记者;在浙江优级师范当音乐美术教师,像一个教师;后来出家为僧,像一个和尚,圆寂后被谥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这是不容易的。他对自己的要求极严格,一丝不苟。你如没有他那样的根基,便写不好那样的字。只有师法他的苦学、恒心,才会出现自己的面目。离开个性,没有艺术!”
在毕业前夕,也有人对我说:“你只会写一个个清清爽爽的字,不会写联笔,本领没有学完全。”我觉得说的是实情,便借了《群玉堂帖》第八卷中米芾自叙学书手迹,还买了《十七帖》《书谱》。可惜《十七帖》中有一大半的字不认识,后来买到注有楷书的《十七帖》,才全部认识而开始练习,也穿插着写过章草。由于求画者较多,画上要题诗落款,字体要有变化,便买了一部《草字汇》。看后才知道每一个字的草法有好几种,这对练习草书平添了浓烈的兴趣。
我进了开明书店当音乐美术编辑后,便一手包办了书籍装帧。有时书名要用隶书,我写了《礼器碑》体字,自己看看很不协调,老板章锡琛也摇摇头说:“你写的是汉隶,古则古矣,但人家不欣赏,你自己也说不协调。那么,我来写一下看,是不是可以好一点,因为我写的是唐隶,笔画比较匀称,容易讨好。”章锡琛提到了汉隶、唐隶的分别,以前我没有学到过。这以后便利用业余时间,逐渐补上这一课。
我早期写草书,进展缓慢。运笔缺少龙飞凤舞之姿,这与见识修养有关,好在不急于求成。我实验用魏碑的笔势来写章草,不断探索。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字除吴昌硕外,还有郑孝胥、朱孝臧、罗振玉、沈寐叟等人,他们的书法都各有欣赏者。在经济上能自食其力,不再依靠家庭,买书就方便得多了。曾购赵之谦手札墨迹多本,印刷不太理想,毕竟长了见识。我的老师丰子恺和马一浮都喜爱沈寐叟的书法,沈的真迹很难得到,只能从印刷品如《寐叟题跋》等书法观摩。我开始搜求墨迹,从不花代价或代价较低的人手,比如马公愚,我和他相熟,就可不花代价取得他的真迹。也常常不花代价请谭泽闿为我写字,因他的儿子是我的学生,他哥哥谭延闿也为我写过字。于右任的字,我弄到五六十件,都不花代价。请章侵(号一山)写草书扇面,或请高振霄、钱崇威这些太史公写字,也只要花一二元钱。这样日积月累的搜求,我手头的墨迹渐多,眼界也就逐渐开阔起来。
静夜,我常常看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书镜》,对照自己的临池情形,使我在理论上有所提高。
几年笔耕,在默默中积累了经验。我抱的决心是:锻炼自己,以修养为主,供人欣赏次之,后来沈雁冰、郑振铎、郁达夫、叶圣陶、陈望道等先生看到我的字,表示喜欢和赞赏。
“君匐,替我写一幅吧!”达夫先生平易近人。
“我的字不行,画张画作为纪念吧!”我恳切地回答。
“好的,谢谢!”他说得很诚挚。
我替他画了一张《蒲公英》,上面用行书写了一篇短短的题记,对这位创造社的元老表示了敬意。
这样,浮名渐渐传播,戴望舒、施蛰存、钱智修、周予同、胡愈之、巴金等作家,都向我要过字,我都认真写好,送给他们。这些人审美要求很高,都比我年长,要我写字,不意味着我的字达到炉火纯青,只是友情和鼓励而已。我的头脑没有发过热。
我爱读金冬心先生的著作,那些沉郁的题跋写得极有个性,清代的世态也跃然纸上。朋友给我看过几幅金冬心的隶书真迹。我摸不透这些隶书的来龙去脉,虽然很羡慕,却没有摹写过。后来《流沙坠简》出版了,珂罗版印刷,每部要银洋一百元,这样大的书价,我是出不起的,便天天去富晋书店站着看,越看越有味道。书店老板知道我迷上了这本书,就问:“你天天来看这部书,是不是想买回去?”
“很想要,就是买不起,书价太贵。”
“你能出多少钱?”
“二十块。再多出就没钱吃饭了。”我说的是实话。
“太少了,不能卖。”老板很沉着。
“你最多能出多少?如比上次说的再加一点,就卖给你。”几天之后,老板再次找我搭话。这不是一本人人喜爱的畅销书。
“加五元,不能再多了。”我把口袋掏空,抱着书,喜洋洋地回到寓所。此后几年间,我常常对它临写把玩。因为练过《石鼓文》和赵之谦的篆隶书,逐渐融合变化,时间稍久,便显出了自己的个性,以天真拙稚见长,庄中寓秀。1946年,《流沙坠简》忽然遗失。解放后翁闿运先生借给我一本,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回去。后来出土的木简更多,《居延汉简》《孙膑兵法》陆续问世,在美学意境上各有千秋。我不断学习,作风渐趋稳定。
十年浩劫,迫使我放下了笔,但还练字,只要稍有闲空,便用指头在衣服上、大腿上不停地写看不见的字。内容不外唐诗,偶尔也写自己的诗。这样做,能使思想集中,不想个人得失,又温习了旧作,不致于忘却。写字,也使我忘了当时的现实,获得了解脱和乐趣。可惜我是近视,写字时不知回避,终于被管“牛棚”的家伙发现。他大声训斥道:“你搞些什么名堂?是不是在搞迷信活动?”
“没有。”
“手指头在身上动来动去做什么?”
“没有什么。”
“不老实!”不过他没有把柄,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凡属“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都要写思想汇报。这件事太乏味。哪有这么多的思想可以汇报呢,真是见鬼!我便每天晚上刻一方印,把钤出的拓本当作思想汇报,第二天带去挂在指定的地方。
“你这是什么汇报?”过了很多天,这种思想汇报被那个家伙发现,他指着拓本质问。
“我学习以后,思想有了感受,就刻成了印,用艺术表现出来。”
“什么艺术不艺术,不老实!艺术不是你所能干的!”尽管他们声色俱厉,我每天送去的订在专栏里的拓本却不翼而飞,原来是被爱好者收去珍藏了。
那时,朋友无法来往,信也不便写,常常遇到的只有刘海粟大师。他每天傍晚由夏伊乔夫人陪同,在复兴公园散步,见到我,他竖起拇指说:“你是艺术家本色,在患难中仍不忘刻印、写字、作画,了不起!”
“练功么,怕时间一长,荒废了,很可惜!”
“我也每天练字作画呢!”他异常信任在把内心秘密告诉我,使我很感动。
回想十年浩劫前,一次我去看他,他拿出一卷画来任我选一张作纪念。我挑了一张《奔马》。不久,我把此画带到北京,给叶恭绰先生看。他说:“海粟可以画得更好!我给你题上一些字吧!”他为我写了元稹的一首五言古诗。十年浩劫中,这幅画在抄家时被拿走,去年又送回来了。这画和字留下了友谊的纪念。
以上是我真实而又平凡的部分回忆。明知起点很低,没有先知先觉的哲理,也没有小说的趣味。(这两条在传记文学中时有所见,也令人不安!)自惭不是书学家、书法家,讲不出理论,读的是很普及的书,练的是很常见的帖,不以孤本秘籍来说得玄乎其玄,高不可攀,也没有值得告诉别人的经验。一知半解,不敢忘记灌溉过我的园丁。青年朋友们看了会大失所望,事实如此,“拔高”的事我不会也不愿做。想到失去的时光,前辈的期望,难免惶悚不安,冷汗涔涔。只有几句肤浅的话赠与青少年们:
书法只是人格修养的体现,人品不高,书品不高。书内求书,不如书外求之。
游泳要下水,写字要临池,蛮干要吃亏,应当向能者和前人请教,少走弯路;但图巧则一事无成。从这一点来说,聪明人最笨,笨人苦干是真聪明。
书法家最好懂得一些篆刻,有利于打好基础,提高鉴赏水平,以拙胜巧,以浑厚胜甜媚,达到较高境地,所谓“书如佳酒不须甜”。
学与不学,干与不干,生命只一次,青春不会再来,还是拼命耕耘吧,收获便在耕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