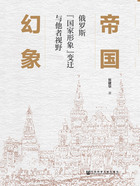
三 俄国:“野蛮的大监狱”
“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事件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破坏美国人眼中的俄国形象,但引发了一场对俄国专制统治与社会黑暗面的大规模批判和揭露,其中对俄国流放制度的讨论,直接导致了美国人眼中俄国形象的巨变。乔治·凯南“并不是最初挑战他帮助建立起来的对俄国的看法的人,但在改变后却提出了对沙皇政府最具影响力的反对”[24]。当时反对乔治·凯南看法的声音,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来自英国的相关研究成果。英国是俄国之外较早开始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进行研究的国家,到乔治·凯南的时代,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这方面的研究著述。当时英国人对俄国的流放制度基本上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着力突出流放生活的黑暗。乔治·凯南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一文中,提到了《伦敦标准》(the London Standard)、《蓓尔美尔街公报》(the Pall Mall Gazette)和托利党人(Tory Party)报纸以及许多英国作家[如传教士亨利·兰斯道尔(Henry Lansdell)1881年发表于《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杂志上的《穿越西伯利亚》(Through Siberia)一文]对西伯利亚流放的研究。乔治·凯南认为这些报纸都具有很强的党派性,这样做是出于国际政治原因,他强调“在整个西伯利亚,都不存在也从没存在过像汞矿(quicksilver mine)这样的东西。在那个被《伦敦标准》形容为‘寂静的没有生命的冰冻沼泽’每个夏天都能生长250000磅烟草”[25]。
第二,与乔治·凯南不同或者说一直被乔治·凯南攻击的观点,来自一些西伯利亚当地人。乔治·凯南认为他们是出于经济和生活状况的不佳而攻击政府。其中最著名的是19世纪80年代西伯利亚地方学者、持地方主义者亚德林采夫(Н.М.Ядринцев)。他是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他对西伯利亚的监狱和流放制度进行批判。1882年亚德林采夫出版了《作为流放地的西伯利亚》(Сибирь как колония),书中提供了大量关于西伯利亚的资料。
早在赴西伯利亚之前,乔治·凯南就对亚德林采夫的思想与著作十分了解,并将其列为最想见到的人。而亚德林采夫同样是在俄国对乔治·凯南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考察计划最感兴趣的人。两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在乔治·凯南去往西伯利亚之前,亚德林采夫还为他亲手写了一份长达七页的“旅行指导”,列出了他认为乔治·凯南应当会见的人和应当参观的地方。1886年乔治·凯南考察西伯利亚结束之后,再次见到亚德林采夫,两人“从革命的可能性谈到托尔斯泰的‘农民田园诗’(Peasant Idyll)”。此后十几年,乔治·凯南与亚德林采夫频繁交流着自己了解的美国与俄国的信息:乔治·凯南提到他经常读的四五本俄国杂志,包括《欧洲通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а)和亚德林采夫主办的《东方评论》(Восточное обзрение)等。他列出自己想要的书,付给需要的钱,由亚德林采夫负责找到。反之,他也寄给亚德林采夫《纽约论坛周刊》(the Weekly New York Tribune)、《纽约先驱报》(the Daily New York Herald)等。亚德林采夫的杂志对乔治·凯南的著作给予关注,亚德林采夫的助手戈拉瓦乔夫(П.М.Головачёв)负责翻译乔治·凯南在《世纪》(The Century)杂志上的文章。1894年亚德林采夫去世,乔治·凯南称亚德林采夫是“这个世界上对于俄国亚洲部分的历史、考古和人类学最见多识广的一个人”。[26]
第三,来自其他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在美国,乔治·凯南也并“不是第一个用‘制度’将这一罪恶记载下来的人,他仅仅是最著名和最有说服力的”[27]。年轻人威廉·杰克逊·阿姆斯特朗(William Jackson Armstrong)在赴西伯利亚旅行后,于1884年写成《俄国的虚无主义运动与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Russian Nihilism and Exile Life in Siberia),这是第一部在俄国之外出版的揭露俄国政府对西伯利亚流放犯处罚的书。这部著作之所以没有获得像乔治·凯南后来的书的影响,仅仅是因为作者的声望不如乔治·凯南。[28]阿姆斯特朗在书中将俄国看成一个“大怪物”(monster)。而“凯南个人对俄国人民的热爱和他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使他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俄国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好的”[29]。这样的观念冲突引发了1885年冬天一场公开的争论。阿姆斯特朗的言论令乔治·凯南生气,但他更想通过一次对西伯利亚流放者状况的实地考察,收集足够的资料与他继续辩论。
1885年5月,在《世纪》杂志资助下,乔治·凯南第四次到俄国,在10个月的时间里,行程1600英里,参观了至少30所监狱。乔治·凯南在1885年5月13日到圣彼得堡后,向帝俄政府官员表示其目的在于:“据我判断,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已被那些有成见的作家极大地误报了。我想,对于这个地方、这些监狱、矿的真实描述,对俄国政府将是有利而非有害的。我公开承诺,我将保卫政府,(你们)大可不用怀疑我有意图在西伯利亚寻找那些会动摇我立场的事实。”[30]俄国政府为他的调查提供了出乎意料的便利。但是,在这次调查之后,乔治·凯南对流放制度的认识却由于大量的证据而完全改变了。1886年8月,乔治·凯南回到美国,在《世纪》杂志连载6篇文章。这些文章在1891年集辑出版,就是著名的《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乔治·凯南开宗明义地表示:“如果现在我所持的看法与1885年所说的不同,那不是因为后来我不诚恳了,而是因为我的观点已经由于大量的证据而改变了。”[31]在这些文章中,乔治·凯南主要从三个层面揭露西伯利亚流放的黑暗。
一是流放条件的艰苦,主要指的是物质层面。与此前的三次俄国之行,即一次从东到西,两次在高加索、欧俄地区不同,乔治·凯南这次的西伯利亚之行,不仅仅是将流放者通常所走的路线行走一遍,而是加入赶赴流放地的流放者队伍,亲身体验沿途行军、监狱生活以及煤矿劳动等。乔治·凯南甚至曾打算和犯人们同住一晚,但因无法忍受监狱内污浊的空气而放弃。他对监狱拥挤和脏乱的情况印象颇深,并得出了政府不愿出钱改善监狱状况的结论。由于越往东走条件越艰苦,流放者所受的刑罚也越重,乔治·凯南对流放制度黑暗的认识也就越深刻。

图1-1 乔治·凯南1885~1886年考察西伯利亚流放路线示意图
二是流放程序的混乱,主要指的是制度层面。在随流放者行进的过程中,乔治·凯南还重视与当地流放者,特别是“政治流放犯”、“不可信任者”(the untrustworthy),以及“通过行政程序被流放者”(exile by administrative process)的直接接触,从他们的经历中了解流放制度。他了解到,西伯利亚流放的惯例除终身监禁的重刑犯,流放者服刑期满后一般会与随行的家人一同留在当地生活,而不再返回欧俄。“简而言之,流放制度就是一个无序的大混乱,其中意外和无常起着几乎同样重要的作用。”[32]
流放程序的无序与随意性,首先体现为“行政流放”权力的滥用。正如一个西伯利亚当地人所说,“它作为一个简单而容易的方式,去处理那些碰巧令人讨厌或碍事但又不方便被审理或者在公正的法庭宣判有罪的人”[33]。早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后期,运用行政流放方式处理政治嫌疑犯的做法就在不断扩大。1882年3月12日,由内务大臣起草,沙皇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Ⅲ)批准一系列关于政治流放的法令,更提出了“不为惩罚已犯的罪,而为防止犯罪”的宗旨。例如,俄国作家沃尔霍夫斯基(Феликс Вадимович Волховский)被流放的罪名就是“属于一个打算在未来的或早或晚的时间推翻现存政府的团体。”[34]其次,在具体的流放过程中,政府并不会去确认被捕的人是否应该被流放,或是确定被流放的人是否与放逐令上的相同,叫相同名字的人被错误流放的事时有发生,流放者联盟(exile artel)[35]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改换姓名。再次,在到达流放地之后,地方行政中猖獗的权力滥用现象同样非常严重。在一个流放犯流放期满的时候,当局通过查看他品行记录的好坏而加上1~5年的流放期的做法并不鲜见。1882年4月,由于发生大量的逃跑事件,靠近尼布楚的卡拉河畔监狱的长官决定“给政治犯一个教训”:剥夺政治犯先前拥有的一切权利,拿走一切不是政府发放的东西,将犯人劳动所得的钱据为官方所有,不允许犯人与妻子、子女见面。在犯人们绝食抗议、濒于死亡之后,这一“将监狱简化为命令”的行为才被制止。[36]
总之,“怪诞的不公正,肆意的残忍,荒唐的‘误认’和‘误解’,使得俄国的行政流放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好像是一个噩梦的独奏音乐会”。[37]
1849年4月23日被帝俄政府宪兵第三厅破获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案”,是1844~1849年活跃于彼得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它的领导人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原名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Петрашевский(Буташевич-Петрашевский)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1-1866],1821年出生于彼得堡一个著名外科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曾经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教父。1932~1839年,彼得拉舍夫斯基在著名的皇村中学学习。后进入仕途,尽管成绩优秀,但因出身和与上司不和仅被授第14级官衔。1840年在外交部担任翻译,同时在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1841年获得法学副博士称号。19世纪40年代初,他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精神危机。他表示:“无论是从女人那里,还是从男人那里,我都找不到任何实现自己信念的东西,我自己注定要为人类服务。”[38]
1856年,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同志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在流放地他不止一次与当地官员发生冲突。到19世纪60年代初,除彼得拉舍夫斯基,其余人均恢复了公民权利重回社会。彼得拉舍夫斯基坚信自己的正义事业,他在给读者的信中说:“既然我准备再一次投入与任何暴力和任何非正义的斗争之中,那么对于我来说绝不能为了获得小利和生活的舒适而离开这条道路。”“我们所有的俄罗斯人,其任何的垂头丧气的实质在于,我们感觉独立性的缺乏,用公民思想来看,我们简直是胆小鬼。尽管在拳头镇压下和任何的刑罚中都有勇士:在与政治的对抗中,我们就是胆小鬼。我们甚至在好友圈里也由于害怕而不敢将自己的思想充分表达。我们大家不得不跟着季节风走。我们把任何当局的行头,特别是将军服都看成雷神(Громовержц)。”彼得拉舍夫斯基在伊尔库茨克与流放犯十二月党人扎瓦利申(Д.Завалишин)发起反对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Н.Н.Муравьев)的斗争。因为此事,彼得拉舍夫斯基被流放到更艰苦的叶尼塞省舒申斯基村。经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姐姐的多方奔走,1861年允许他移居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864年彼得拉舍夫斯基因政治活动被驱逐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866年5月,彼得拉舍夫斯基被转移到距离叶尼塞斯克(Енисейск)100俄里的别林斯基村,当年12月6日因脑出血在此病逝。赫尔岑立即在《钟声》上发表了讣告:“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叶尼塞斯克省的别林斯基村意外去世,终年45岁。他为后代留下了为俄国自由而牺牲于政府的迫害者的纪念碑。”[39]
三是流放对人性的摧残,这主要指的是精神层面,特别是对于一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而言的。乔治·凯南在托木斯克(Томск)结识亚历山大·克鲁泡特金公爵(Александр Кропоткин)的故事代表了当时许多政治犯的人生轨迹:他并不是什么革命者,只是因为是一个俄国政府讨厌的人——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彼得·克鲁泡特金(Петр Кропоткин)公爵的弟弟。1858年他在圣彼得堡大学第一次被捕,原因是藏有美国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论自助》(Self-Reliance)一书。1876年或1877年,他第二次被捕,以“不可信任”(untrustworthiness)的罪名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Минусинск)。由于当地只有他一个政治犯,当局打算再将他送到图鲁克汉斯克(Туруханск),妻子决定送孩子回欧俄后陪他一同前往。后来,他又被转送到托木斯克。在托木斯克,乔治·凯南参观了克鲁泡特金的图书馆。在乔治·凯南离开托木斯克的前一天,克鲁泡特金来到乔治·凯南的房间,托他带信到欧洲。晚上克鲁泡特金又来,要毁掉一切写有他兄长彼得·克鲁泡特金名字的信封。7月25日,亚历山大·克鲁泡特金自杀。乔治·凯南在《东方评论》(Восточное обзрение)上得到克鲁泡特金的死讯,大为叹息。
在托木斯克,乔治·凯南第一次感受到流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在1885年8月26日从托木斯克寄给《世纪》杂志社董事的信中,他写道:“流放制度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这个省的总督昨天直白地告诉我,托木斯克监狱的状况很糟糕,但他无能为力……我先前对政治犯的待遇所写和所说的那些,看上去大体还是准确和真实的——至少就西伯利亚而言是这样。但我对于他们人格的那些先入为主的想法被严重动摇了。”[40]在乔治·凯南看来,政治犯们都是平和、守法的公民,他们拥有丰富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在别的环境,(他们)会致力于给国家有价值的服务……他们在监狱,并不是因为缺少作为一个公民必需的道德和爱国心。”[41]同样在俄国统治阶级内部,也有部分有识之士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持批评态度。例如,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总督巴拉诺夫(Николай Баранов)认为政治流放“不是重塑而是摧残人的品性,引起自杀,不能创造对社会和王位有用的人。而(在监狱中)与那些真正的政府的敌人接触,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反政府者,是环境让他们发展出了革命思想”[42]。
回国后的乔治·凯南果断抛弃了那些曾令自己名声斐然的观点,将关于俄国的新的真相告诉美国民众。《世纪》杂志对乔治·凯南关于流放制度的系列文章给予极高的评价,说这是“《世纪》杂志获得过的最高的荣誉和特权”[43],堪称“西伯利亚流放者‘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乔治·凯南文章的带动下,这一时期《世纪》杂志每期发行量都超过200000册,[44]影响很大。1889~1898年,乔治·凯南在各地发表演说超过800次,大部分都是抨击俄国与流放制度的。
《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作为第一部细致地对俄国政府民主政策进行抨击和被美国人广泛阅读的书,乔治·凯南对西伯利亚的研究,或许不可以被认为革命性的,但那至少是一个认识逐渐进化的开始。”[45]此后的许多年中,虽然他自己不愿意这样说,但是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十分确信,乔治·凯南将俄国塑造成了一个“大监狱”形象。他“已经激起了美国人同情和愤慨的热情,让美国人更能感受和理解俄国造反者”[46]。从前美国人出于对革命者实施暴力的恐惧而对沙皇政府加强流放制度的认同和支持一扫而空,正如1888年马克·吐温(Mark Twain)对乔治·凯南的书的评价:“如果地那明(解痉药)是唯一能解决这些状况的药物,那些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地那明!”[47]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对流放制度的评价为切入点,以乔治·凯南为代表,美国人眼中的俄国形象经历了史上最大的一次转变,这个转变无论是对美国还是俄国,无论是对当时还是20世纪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也不管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是非常迅速而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