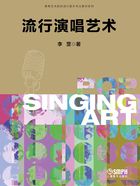
七、流行歌曲的文化性
流行音乐是近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休闲娱乐内容来源,它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不论是在夜总会或现场演唱会,也不管是透过电影、电视剧的间接传播,或是如今盛行的直播平台,对许多人而言,流行音乐的确是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一种娱乐内容。有关专家指出,我们将歌曲纳入生活、将节奏纳入身体,歌曲和节奏有一种随意可取的参考价值,可以让人立刻接受。
流行音乐也和政治议题与社会变革有所关联。在1969年,有50万人聚集在纽约近郊的伍德斯托克,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而这个活动的诉求之一既是抗议美国持续参与越战。在1980年代,流行音乐成为一连串超大型活动的焦点,向全球广为传播。自1960年代晚期以来,流行音乐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媒体研究及社会学相关学科研究的重点。
1960年代中期流行音乐的转变体现在,三分钟的商业流行歌曲被更长的乐曲所替代,并倚重于乐手的即兴演奏技巧与新兴电子音效。流行音乐美学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反文化的年轻人渴望尝试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其要件就是使用迷幻乐和皈依东方宗教,以拒绝西方科技统治。
软金属乐团的出现使得重金属音乐在1980年代逐步转向较为抒情的风格,歌词与乐风进入了典型的“邦乔维风格”。因而比先前的重金属风格能够吸引更多的女性听众。在后工业时代的都市环境中,这些元素对年轻人的生活造成了冲击。
西方社会经历了重金属、朋克的喧嚣时代,在后金属年代,英国出现了雷鬼音乐。这是青年人在寻找原创音乐与民族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产物。雷鬼乐在牙买加通过鲍勃马利和彼得托施等艺人的作品与拉斯达宗教运动相结合,体现了雷鬼音乐对英国非裔加勒比海青年的文化意义。如果说雷鬼艺人参与并推动了英国音乐反种族歧视运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一点绝不夸张。
说唱乐与嘻哈文化起源于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地区,说唱乐被美国的非洲裔与西班牙裔青年当作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如贫穷、种族歧视、自尊等)的工具。后来,说唱乐从美国传向欧洲和日韩,形成了新青年的时尚文化。
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业革命的来临,民间的音乐创作与流变分别跟空间与时间上的两种变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音乐实际上镌刻的是从乡村到城市、从故乡到异乡的集体迁徙经验,比方说美国南方黑人从棉花田向芝加哥的迁徙,造成了爵士乐与蓝调的兴起;再如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朝鲜半岛战争前后的漂流,造成了上海流行曲风在台湾的流行。
1975年,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了一个小型音乐会,作品唱的是余光中的诗,余光中是当时极受台湾青年推崇的诗人,此音乐会被台湾乐界视为“民谣(或民歌)运动”的起点。
台湾民歌早期的作品一般是歌咏山水之美、青春之情,旋律清新自然、歌词朴素无华,叶佳修、苏来、李建复等歌手,靳铁章、毕心一、毕奂一、林建助、许翰君、陈云山、黄大城、王新莲、吴楚楚等词曲作者是当时民歌运动的主力军,他们的创作吸引了大批台湾青年。而随着侯德健、罗大佑、李泰祥的介入,民歌运动有了质的飞跃,比初期的淳朴无瑕多了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大量的歌词采用名家的诗作,如三毛、余光中、赖西安、罗门、席慕蓉、李敖、蒋勋等台湾作家,民歌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侯德健代表作是为李建复创作的《龙的传人》;罗大佑的第一首作品是刘文正的《歌》,第一张制作专辑是张艾嘉的《童年》;李泰祥的处女作是为齐豫创作的《橄榄树》。但他们最好的作品还是自己的专辑,例如侯德健的《三十以后才明白》,罗大佑的《之乎者也》。在70年代的大时代背景下,激情和理想共存,成为台湾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而影响了当时的艺术、文学和社会观念,一大批台湾作家从被动参与到主动介入,也促进了台湾地区音乐的自我觉醒。
当时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歌手和词曲作家或多或少地都受到欧美流行乐的影响,有的歌星干脆扯起了摇滚的大旗,林子祥、庾澄庆、李恕权、蓝心湄等歌星都在摇滚歌曲的制作和演唱方面有所建树。20世纪80年代,摇滚乐传入我国大陆,那时的歌坛,不用说摇滚乐,就是流行歌曲都被视为异端之音,我们的流行音乐迈着先天不足、后天缺氧的沉重步伐,走进了90年代,尽管它无益于百姓的脱贫致富,也无益于经济的繁荣,但毕竟人民需要它。广大知识青年对人生的迷惘在崔健的一曲《一无所有》中一下子宣泄出来。从此,青年人对摇滚乐的痴迷一发而不可收。1990年北京现代音乐演唱会上,黑豹、唐朝、超载等六支风格各异的摇滚乐队同台演出他们各自的摇滚作品,使得全场观众情绪振奋,巨大的音乐声、欢呼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观众席上,几乎所有的歌迷都从头至尾站在那里随着节奏不停地摇动着身体,直到全场演出结束,歌迷们还站在那里不停地挥动手臂。此情此景,几乎是美国摇滚乐演出场面的翻版。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看完音乐会后激动地说:“这样有力度的演唱会真过瘾,我太兴奋了。”据当时主办单位透露,两场演出的三万张门票顷刻售罄。
此后的摇滚乐虽然没有90年代那么辉煌,但是一些现象级的摇滚乐队和音乐人也不断创造着属于中国的摇滚乐。郑钧的《赤裸裸》、天堂的《皇城根》、超载的《破碎》、鲍家街43号的《真的需要》都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算是将第一代摇滚人的接力棒承接了下来。还有1993年签约台湾滚石唱片的“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各自推出专辑即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以他们的中国摇滚影响了一代人。
华人摇滚乐的发展,历史虽然不算太长,但其发展的速度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被誉为“中华第一摇滚”的崔健,以其超前的意识和对摇滚乐的敏感,创作了中国的第一批摇滚歌曲,他的《一无所有》在大陆风靡后,又在台湾“龙虎榜”上几度荣登榜首,从而形成了中国摇滚的独特风格。崔健为第十一届亚运会集资100万元而举办的个人演唱会,在北京、郑州、武汉、西安、上海、成都等十一个城市巡回演出数日,气氛空前热烈,报界评论说:“整个演出呈现一种狂放的艺术品位,乐曲节奏如汹涌澎湃的海潮一般,带着一种强大的冲击力,人们从他那充满强烈的绝望与呐喊声里,看到了自己。”
流行音乐,永远是文化的载体,伴随着城市化、都市化的倾向,流行音乐永远会镌刻上当代文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