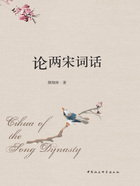
第一节 药名词——词的独特的审美形式
“词”作为诗歌的种类之一,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形式,最大程度地展示了汉语言的诗性意象和审美魅力,呈现古典人文心理对于形式美的执着和沉迷。李清照标举词“别是一家”[1]之说。孟称舜云:“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词者,诗之余而曲之祖也。乐府以皦劲扬厉为工,诗余以宛丽流畅为美。”[2]近人王国维亦认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3]词,倚仗汉语言特有的审美意象和空间形式,又融入了华夏民族丰厚的音乐文化,形成极其圆融庄严又婉丽空灵的形式美。自北宋以降,对于词之形式美的眷注成为文化人的普遍意识,吴处厚的词话对于形式美的瞩目亦为北宋时期的文化语境使然。在《青箱杂记》中,吴处厚表现出对“药名词”的浓厚兴趣。他对陈亚的“药名词”尤为推崇。《青箱杂记》云:“陈亚,扬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盖近世滑稽之雄也。尝著药名诗百余首,行于世。……又尝知祥符县,亲故多干借车牛,亚亦作药名诗曰:‘地居京界足亲知,措借寻常无歇时。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览者无不绝倒。亚常言:‘药名用于诗,无所不可,而斡运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亚曰:‘可。’沉思良久,因朗吟曰:‘“布袍袖里怀漫刺,到处迁延胡索人。”此可以赠游谒穷措大。’闻者莫不大笑。”又载:
(陈)亚与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当轴,将用之,而为言者所抑。亚作药名《生查子·陈情》献之,曰:“朝廷数擢贤,旋占凌霄路。自是郁陶人,险难无移处。也知没药疗饥寒,食薄何相悮。大幅纸连粘,甘草归田赋。”亚又别成药名《生查子·闺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其二曰:“小院雨其凉,石竹风生砌,罢扇尽从容,半下纱厨睡。起来闲座北亭中,滴尽真珠泪。为念婿辛勤,去摘蟾宫桂。”其三曰:“浪荡去未来,踯躅花频换。可惜石榴裙,兰麝香销半。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弦断。拟续断朱弦,待这冤家看。”亚又自为亚字谜曰:“若教有口便哑,且要无心为恶。中间全没肚肠,外面强生 角。”此虽一时俳谐之词,然所寄兴,亦有深意。亚又别有诗百余首,号《澄源集》。[4]
角。”此虽一时俳谐之词,然所寄兴,亦有深意。亚又别有诗百余首,号《澄源集》。[4]
从以上“药名词”来看,其表情言意的艺术功能较为显明,词章中巧妙融入数种中药名称,言情之中隐含着诙谐。前一首委婉陈述了谗言者对自己仕途的阻拦,并抒发苦涩无奈的情绪和表明归隐田园的选择,其中融入幽默的笔调,进行自我宽慰和解嘲;后三首拟闺阁思妇的口吻,抒写了现实生活中离别夫妇的相思之情。诗词中均恰到好处地点缀着中药名称,与词之表意密切地联结起来,没有生硬杂糅之感,显现了作者高超的创作技巧。
由此可见,所谓“药名词”,即是在词章里融入中药药名,以构成具有审美趣味的艺术情境。众所周知,中医药是华夏古老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渗透到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为古人所耳熟能详,心理上容易滋生亲近情绪。所以,以它入词,能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从文艺理论的观点来考察,中药名,在语言学意义上,一方面作为物质对象的命名符号,另一方面则具有某种象征性的人文意蕴。以药名入词,实则呈现了古人对于汉语言的诗意游戏的创造性智慧,既见出汉文化特有的韵致,又显露词之独异的形式美。吴处厚对于“药名词”的关注,应该说是出于对“形式美”偏爱的艺术视角。“药名词”,依现代美学看来,是近乎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5]这一理论界定。从更宽泛的意义而言,吴处厚对于“药名词”的喜好,与康德、克罗齐的形式主义的艺术主张有心灵相通之处。其潜在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对于传统的文艺观具有纠偏的作用。因为在某些士大夫眼里,词为“末道”“小技”,与传统的“载道”“宗经”的文章不能相提并论。
从文学的一个具体的审美功能来看,“游戏”是其构成之一。如果我们从更宽广的美学视角来看,“游戏”(Spiel)概念如伽达默尔所言“在美学中起过重大作用”,他认为:“游戏确实被限制在表现自我上。因此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现(Selbstdarstellung)。而自我表现乃是自然的普遍的存在状态……游戏最突出的意义就是自我表现。”[6]从这个理论视点看,药名词的写作动机之一,无疑有语言游戏的目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人运用“中药”名词进行语言的智慧游戏,而游戏又凭借于“词”这种文学的新样式得以呈现。在游戏的过程中,既使轻松幽默的情绪得以释放,也委婉含蓄地表现出个体的意趣,当然,又客观地达到表现自我的写作意图。这种语言游戏方式,体现出中药知识和艺术智慧的交融,体现出生活经验和文学技巧的渗透。吴处厚的词话对于药名词的关注具有深层的美学意义。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单纯以药名入词,容易远离文学本位。伯固对于“药名词”的垂青,不免超脱社会历史而未有思想意蕴难免落入纯粹的词语游戏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