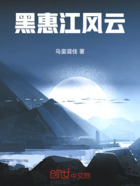
第26章 松山遗影:老广的故事(2)
二、星光下的约定与历史的回响
此后的日子里,乌蛮滋佳像是推开了一扇沉重而神秘的大门。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在岔河边跟着钱方叔摸鱼、学编竹蚂蚱。他成了后山放羊坡上的常客。有时是帮着老广把走散的羊羔赶回群里,有时是静静地坐在那块大石头上,听老广用沙哑的嗓音,在松涛声里,一点一点地拼凑那些尘封在硝烟与血泪中的碎片。
老广告诉他,松山战役最惨烈的那一天,炮火把半边天都映成了诡异的紫红色,浓烟滚滚,遮天蔽日,连平日里盘旋觅食的老鹰都不敢飞过那片死亡空域。他也会在难得的平静时刻,带着一丝遥远的温暖回忆道:“我们广西老家啊,有种树叫木棉,春天开花,那花红得哟……像天边烧起来的晚霞,一大片一大片的,好看得很……”每当这时,他那双总是布满阴霾的眼睛里,会短暂地闪烁起一点微弱的光芒,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故乡那片绚烂的红云。
村上其他几个同样沉默寡言的老兵,渐渐都知道了这个总爱往后山跑、缠着老广问东问西的彝族少年。瘸了一条腿、走路一颠一颠的王大爷,会在他路过自家门口时,偷偷塞给他一个刚烤好的、香喷喷的玉米棒子,粗糙的大手拍拍他的头,什么也不说。独眼的李阿伯,则在一个阳光晴好的下午,神秘兮兮地把他叫到自家后院,从一个破旧的木箱底翻出几个磨得发亮的黄铜弹壳,耐心地教他用小锤子和钉子,在弹壳上敲出小孔,再用细麻绳穿上,做成一个能发出清脆声响的小风铃。“风一吹,叮铃铃响,好听吧?比你们小孩子玩的竹哨子响多了!”李阿伯咧开缺了门牙的嘴笑着,那只完好的眼睛里带着一丝难得的顽童般的得意。
每当月圆之夜,老核桃树下又会响起低沉而苍凉的歌声。老广、王大爷、李阿伯他们聚在一起,喝着廉价的包谷酒,哼唱着那首让乌蛮滋佳听不懂词、却能清晰感受到无尽悲怆的《松花江上》。那歌声仿佛有生命,带着沉甸甸的乡愁和无言的伤痛,穿过老槐树沙沙作响的枝叶,飘向深邃的夜空,飘向那永远无法再回去的远方。
与此同时,乌蛮滋佳与钱方的友谊也在岔河的水波和竹篾的清香中日益深厚。钱方不仅教会了他辨识水纹鱼踪、编织活灵活现的小动物,更在他一次次目睹钱方将辛苦所得无私分给他人、自己却默默挨饿时,感受到了另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那个星光璀璨的夜晚,在钱方简陋却干净的小院里,乌蛮滋佳听着钱方讲述自己孤苦的童年,看着他眼中闪烁的泪光,第一次真正触摸到了这个外表粗犷、内心却无比柔软的汉子深藏的孤独与善良。他郑重地许下了要教钱方认字、要当老师的诺言。钱方宽厚的手掌落在他肩头的温度,和那声带着哽咽的“谢谢你,小乌蛮”,让他觉得自己瞬间长大了许多。
然而,平静的日子下潜藏着不安。一天傍晚,乌蛮滋佳帮阿妈去村口小杂货铺买盐巴。远远地,他看见老核桃树下站着几个异常挺拔的身影——正是老广、王大爷和李阿伯他们!他们不再是平日佝偻沉默的样子,而是像即将出征的士兵,站得笔直。每个人手里都紧紧握着一件东西——不是农具,而是几把磨得寒光闪闪、却难掩锈迹的刺刀!他们脸上的神情是乌蛮滋佳从未见过的决绝,甚至带着一种赴死的凛然。
乌蛮滋佳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顺着老兵们凝重目光的方向望去——一支穿着统一土布军装、打着绑腿的队伍,正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从村外的大路上向岔河村走来!队伍前面的人扛着枪,枪口在夕阳下闪着冷光。
恐惧瞬间攥紧了乌蛮滋佳的心脏。他想起了老广描述的枪林弹雨,想起了那些倒在血泊中的年轻士兵。他几乎要尖叫出声,想冲过去把老广他们拉开。他害怕下一秒,枪声就会撕裂岔河傍晚的宁静,鲜血会染红这片熟悉的土地。
时间仿佛凝固了。队伍越来越近,脚步声清晰地敲打着地面。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紧张时刻,走在队伍最前面、看起来像军官模样的年轻人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抬起手,身后的队伍也齐刷刷地停了下来。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那个年轻军官对着老核桃树下的老兵们,挺直腰背,抬起右手,敬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带着无比敬意的军礼!他声音洪亮,清晰地穿透了暮色:
“各位前辈!辛苦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如同惊雷般在老广等人耳边炸响。他们呆立在原地,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手中的刺刀再也握不住,“当啷”、“当啷”几声脆响,纷纷掉落在坚硬的土地上。老广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敬礼的年轻军官,嘴唇剧烈地哆嗦着,胸膛剧烈起伏。终于,他颤抖着,极其缓慢地、甚至带着几分笨拙和生疏,却用尽了全身力气,艰难地抬起自己的右手,回了一个同样庄重的军礼!浑浊的、滚烫的泪水再也无法抑制,顺着他脸上刀刻般的深深皱纹,汹涌地滑落下来,砸在脚下的泥土里。王大爷和李阿伯也早已是老泪纵横。
那一刻,仿佛有无形的坚冰在阳光下轰然碎裂。
后来,乌蛮滋佳才从大人们压低的议论中得知,那支队伍是奉命来接收和安置流散在各地的国民党旧部人员的。老广他们没有被当作敌人对待,而是被详细登记了信息,获得了合法的身份证明,成为了岔河村真正的一员,和当地彝族腊罗巴人生活在一起。压在老兵们心头多年的巨石,似乎终于被挪开了一丝缝隙。